1992年的夏天格外闷热。我蹲在自家小院的水井旁,用湿毛巾一遍遍擦着汗涔涔的脖子。父亲上个月突发脑溢血住院,花光了家里所有积蓄,还欠下一屁股债。我正盘算着明天该去哪家亲戚再借点钱时,院门被轻轻叩响了。
"请问,卫东在家吗?"
这声音像一缕清泉,瞬间浇灭了我心头的燥热。我猛地站起身,毛巾掉进了水桶里。这声音我太熟悉了——林芊雪,我的小学同桌,现在的镇中学语文老师,也是我最大的债主之一。
"在、在的!"我慌忙整理了一下皱巴巴的汗衫,三步并作两步跑去开门。
院门吱呀一声打开,林芊雪站在夕阳下,穿着一件淡蓝色连衣裙,头发松松地挽在脑后,手里拿着一个帆布包。十年不见,她出落得更加漂亮了,皮肤白皙,眉眼如画,只是眼角多了几丝我从未见过的疲惫。
"芊雪..."我嗓子发干,不知该说什么好。
她微微一笑,那笑容让我想起小时候她分给我糖吃时的模样。"好久不见,卫东。"
我赶紧把她让进院子,手忙脚乱地搬来竹椅,又用袖子擦了擦上面的灰尘。"坐、坐吧。我给你倒茶。"
"不用麻烦了。"她轻轻按住我的手腕,那触感让我心跳漏了一拍,"我来是有正事要谈。"
我顿时明白了她的来意,羞愧感像潮水一样涌上来。三个月前,父亲住院急需用钱,我走投无路之下硬着头皮去找了林芊雪。那时她二话不说借给我三千块钱——相当于她半年的工资。
"芊雪,钱的事..."我搓着手,不敢看她的眼睛,"能不能再宽限几天?我找到工作立马还你。"
院子里静得可怕,只有知了在不知疲倦地叫着。我偷瞄了她一眼,发现她正盯着院子里那棵老槐树发呆——那是我们小时候经常一起乘凉的地方。
"卫东,"她突然转过头,直视着我的眼睛,"你还记得我们十岁那年,在这棵树下说过什么吗?"
我愣住了。记忆像被拨动的琴弦,嗡嗡作响。那年夏天,我们并排躺在槐树下的凉席上,她突然说长大后要嫁给我。我当时笑她不知羞,她却一本正经地说:"我说真的,卫东。我林芊雪说到做到。"
"我..."我的喉咙像被什么堵住了。
林芊雪的脸突然红了,她低下头,声音轻得几乎听不见:"其实...以身抵债也行..."
"什么?"我以为自己听错了。
她抬起头,眼睛里闪烁着我看不懂的光芒:"我说,如果你实在还不上钱,可以...可以和我结婚。成为一家人就不用还了。"说完她自己先笑了,但那笑容里带着几分羞涩和期待。
我的大脑一片空白。这是什么情况?讨债讨出个媳妇来?
"芊雪,你别开玩笑了。"我干笑两声,"你现在是老师,有文化有地位,我连个正经工作都没有..."
"我没开玩笑。"她突然严肃起来,"卫东,你知道这些年我为什么一直没结婚吗?"
我摇摇头,心跳如擂鼓。
"因为我一直在等你。"她说完这句话,脸已经红到了耳根,"我知道你可能觉得我疯了,但小时候说过的话,我一直记在心里。"
院子里的空气仿佛凝固了。我看着她坚定的眼神,突然意识到她是认真的。这个认知让我既震惊又感动,还有一丝难以言喻的喜悦。
"芊雪..."我刚想说什么,院门又被推开了。
"东子!东子!好消息!"我的发小李大壮风风火火地闯进来,看到林芊雪后猛地刹住脚步,"哟,林老师也在啊。"
林芊雪迅速恢复了平常的端庄模样,站起身理了理裙摆:"李大哥。"
李大壮狐疑地看看我又看看她:"我是不是来得不是时候?"
"没有的事。"我赶紧说,"什么好消息?"
"县里机械厂招工,明天报名!你不是会修拖拉机吗?正好对口!"李大壮兴奋地说。
这个消息确实让我心头一喜。如果能进机械厂,不仅父亲的医药费有着落,我还能...我偷偷看了眼林芊雪,发现她正微笑着看我,眼里满是鼓励。
"太好了!我明天一早就去。"我说。
李大壮又说了几句就告辞了,院子里又只剩下我们两个人。尴尬的沉默再次降临。
"那个..."我们同时开口,又同时停住。
"你先说。"我挠挠头。
林芊雪深吸一口气:"卫东,我刚才的话是认真的。但我不希望你因为钱的事勉强自己。如果你进了机械厂,钱可以慢慢还..."
"不是钱的问题。"我打断她,鼓起勇气直视她的眼睛,"芊雪,我只是不敢相信...你这样的好姑娘,怎么会看上我这样的..."
"因为你善良、正直,从小就是。"她轻声说,"记得五年级那次我摔断腿吗?是你每天背我上下学,整整两个月。"
我没想到她还记得这些。那时候只觉得是应该做的,从没想过会被人记这么久。
"而且..."她犹豫了一下,"我知道你去年偷偷给王奶奶家修屋顶,还帮她挑水。你一直都是这样的人,卫东。"
我惊讶地看着她:"你怎么知道这些?"
"因为我..."她咬了咬嘴唇,"我一直关注着你,卫东。即使你从没注意过我。"
这句话像一把锤子,重重敲在我心上。我从未想过,在我为生活奔波劳碌的日子里,竟有人一直在默默注视着我。
夕阳的余晖洒在她脸上,为她镀上一层金色的光晕。我突然发现,眼前这个女孩比记忆中任何时候都要美丽。
"芊雪,如果我进了机械厂..."我听见自己说,"你愿意...和我处处看吗?"
她的眼睛一下子亮了起来,像星星落进了池塘:"真的?"
"嗯。"我点点头,突然觉得压在肩上的重担轻了许多,"不过得等我还清你的钱..."
"傻瓜。"她笑了,那笑容让我想起小时候她偷塞给我的糖果,甜得让人心颤,"都说了,成为一家人就不用还了。"
我们相视而笑,院子里的老槐树沙沙作响,仿佛也在为我们高兴。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辗转反侧。窗外的月光洒进来,照亮了桌上林芊雪"忘"在我家的手帕——淡蓝色的,角落里绣着一朵小小的雪花。我知道这不是遗忘,而是一个信号,一个约定。
明天,我要去机械厂报名,要开始新的生活。而这一次,我不是一个人了。
第二天天还没亮,我就起床了。穿上唯一一件像样的白衬衫,对着破镜子刮了胡子,还特意用湿毛巾把翘起的头发压了压。出门前,我犹豫了一下,还是把林芊雪留下的手帕折好放进了口袋。
县机械厂门口已经排起了长队。我踮脚数了数,前面至少有三十多人,而招工告示上只写着"招五名熟练技工"。我的心沉了下去。
"嘿,卫东!"李大壮在队伍前面冲我招手,"快过来!我给你占位置了!"
我挤过去,感激地拍了拍他的肩。李大壮神秘兮兮地凑到我耳边:"听说这次主考的是赵厂长本人,特别严格。你可得好好表现。"
正说着,厂门开了,一个穿着蓝色工作服、国字脸的中年男人走出来,手里拿着花名册。这就是赵厂长,我听说过他——退伍军人,做事雷厉风行。
"都听好了!"赵厂长的声音像洪钟,"今天考核分两部分:笔试和实操。不及格的直接回家!"
笔试题目对我来说不算难,都是些基础机械原理。我偷瞄四周,看到不少人抓耳挠腮,心里稍微有了点底。
实操考核在厂区后院进行。三台出了故障的柴油机排成一排,考官要求我们在半小时内找出故障并修理。
我排在第三个。前面两个应聘者满头大汗地折腾了半天,机器连响都没响一下。轮到我了,我深吸一口气,蹲下来仔细检查。
油路堵塞,火花塞积碳,还有调速器弹簧松了——十分钟内我就找到了所有问题。拿起工具时,我的手出奇地稳,仿佛这些金属部件是我手指的延伸。扳手、螺丝刀在我手里像活过来一样,精准地找到每个需要它们的位置。
"启动试试。"二十分钟后,我擦了擦额头的汗对考官说。
考官怀疑地看了我一眼,拉动了启动绳。柴油机"突突突"地响了起来,声音均匀有力。
"好小子!"赵厂长不知什么时候站在了我身后,用力拍了下我的后背,"哪学的这手艺?"
"自学的。"我老实回答,"家里拖拉机老坏,拆多了就会了。"
赵厂长眯起眼睛打量我:"明天来上班,试用期一个月。工资六十八块,转正后八十四。"
我高兴得差点跳起来,这可是比种地强多了!回家的路上,我特意绕到镇中学,想等林芊雪下课告诉她这个好消息。
放学的铃声响起,学生们蜂拥而出。我站在校门对面的槐树下,远远看见林芊雪抱着教案走出来,身边围着几个问问题的学生。她耐心解答的样子温柔极了,阳光透过树叶在她身上洒下斑驳的光影。
"芊雪!"我忍不住喊了一声。
她抬头看见我,眼睛一亮,快步走过来:"怎么样?"
"录取了!明天上班!"我忍不住咧嘴笑了,"工资六十八呢!"
"太好了!"她高兴得差点跳起来,随即意识到学生们还在看,赶紧恢复了老师的端庄模样,但眼里的笑意藏不住,"我就知道你能行。"
我们沿着林荫道慢慢走,她问我考核的细节,我手舞足蹈地比划着修柴油机的过程。说到兴奋处,我无意中抓住了她的手,两人同时一愣,但谁都没松开。
"那个..."我红着脸转移话题,"以后中午我能去找你吃饭吗?厂里离学校不远。"
"好啊。"她低头看着我们交握的手,声音轻得像羽毛,"我...我给你带饭吧。厂里食堂油水少。"
就这样,我们开始了奇妙的"午餐约会"。每天中午,林芊雪都会带着两个铝制饭盒来厂里找我。我们躲在厂房后那棵老槐树下吃饭,就像小时候一样。她的厨艺很好,总是变着花样做菜,我的饭盒里永远有最大块的肉。
厂里的工友很快就注意到了这个"规律"。
"哟,卫东,你那漂亮媳妇又来送饭啦?"每当我提前收拾工具,总能听到这样的调侃。我嘴上说着"别瞎说",心里却甜滋滋的。
我的机械天赋在厂里得到了充分发挥。别人要学半个月的操作,我三天就能掌握;老师傅修不好的机器,我捣鼓几下就能重新运转。一个月不到,赵厂长就把我调到了技术组,工资涨到了九十块。
那天中午,我兴奋地等着林芊雪,想告诉她这个好消息。可她迟迟没来,我正担心着,厂里突然响起了刺耳的警报声。
"全厂紧急集合!"大喇叭里传来赵厂长焦急的声音,"生产线主轴故障,停产了!"
我跑到主车间,看到一群人围着一台大型机床束手无策。赵厂长急得满头大汗:"修不好今天就得损失上万元!谁能修?奖金一百块!"
几个老技工轮流检查后都摇头。我鼓起勇气站出来:"厂长,让我试试。"
所有人都看着我,眼神里满是怀疑。我才来一个月,还是个毛头小子。
"你?"赵厂长犹豫了一下,但情况紧急,"行,死马当活马医吧!"
我钻进机床底部,仔细检查传动系统。油污弄脏了我的白衬衫,汗水顺着额头流进眼睛,但我顾不上擦。这是一种我从未接触过的进口设备,但机械原理大同小异。
"需要拆开齿轮箱。"我钻出来说,"可能是主轴轴承碎了。"
"拆?"技术组长老张瞪大眼睛,"这设备进口的,拆坏了谁负责?"
"不拆今天生产就泡汤了。"我坚持道。
赵厂长一咬牙:"拆!卫东,你负责!"
在众人怀疑的目光中,我小心翼翼地拆开了齿轮箱。果然,主轴轴承碎了三颗滚珠,卡死了传动系统。更麻烦的是,这种特殊轴承厂里没有备件。
"我有办法。"我跑回宿舍,从床底下翻出几个不同型号的轴承,这是我平时收集的旧零件。经过比对,我发现可以用两个小轴承叠加代替那个大轴承。
"这能行吗?"老张怀疑地问。
"理论上受力是一样的。"我专注地安装着改造后的轴承,手稳得像在拆炸弹。
三个小时后,机床重新运转起来,声音比原来还要平稳。赵厂长激动地拍着我的肩膀:"好小子!从今天起,你就是技术组长了!工资一百二!"
工友们欢呼着把我抛向空中。透过人群的缝隙,我看到林芊雪不知什么时候来了,站在车间门口,眼里闪着泪光,手里还拎着两个饭盒。
下班后,我们在老槐树下分享了已经凉了的午餐。她特意煮了红烧肉庆祝我升职。
"慢点吃。"她笑着看我狼吞虎咽,"又没人跟你抢。"
"芊雪,"我突然放下筷子,认真地看着她,"下个月发工资,我就能先还你一部分钱了。"
她摇摇头:"不急。你现在是技术组长了,要用钱的地方多着呢。"顿了顿,她又轻声说:"其实...那钱本来就是我存着当...当嫁妆的。"
我的心猛地跳了一下。夕阳透过树叶,在她脸上投下细碎的光影,睫毛在脸颊上投下小小的阴影。我鼓起勇气,握住了她放在饭盒边的手:"芊雪,等我还清所有债务...你愿意嫁给我吗?"
她的手在我掌心轻轻颤抖,却没有抽走:"傻瓜...我不是早就答应过了吗?十岁那年,在那棵槐树下。"
我们相视而笑,远处工厂下班的铃声悠扬地响起,惊起了槐树上的一群麻雀。
那天晚上,我在宿舍用废木料雕刻一匹小马——就像小时候送给她的那匹一样。月光从窗户洒进来,照在我粗糙的手和渐渐成型的小木马上。我想象着把它送给林芊雪时她惊喜的样子,心里满是前所未有的踏实和期待。
机械厂的活越来越顺手,我甚至开始偷偷研究厂里那些进口设备的图纸,梦想着有一天能自己设计机器。而每天中午与林芊雪在老槐树下的午餐,成了我最期待的时刻。
有时候她会带着学生作业来批改,我就坐在旁边看她认真工作的侧脸;有时候我会给她讲解机械原理,她虽然听不懂却总是专注地点头。我们之间的默契越来越深,一个眼神就能明白对方的心思。
一个周末,林芊雪邀请我去她家吃饭。我紧张得提前三天就开始准备,买了新衬衫,还特意理了发。她家在小镇教师楼,整洁温馨。当她从卧室拿出一个褪色的小木盒时,我的心跳漏了一拍。
"还记得这个吗?"她打开盒子,里面是我十岁时用桃木刻的小马,已经有些发黑了。
"你还留着..."我轻轻抚摸那个粗糙的雕刻,没想到她珍藏了这么多年。
"我所有的宝贝都在这儿。"她翻开一本相册,里面全是我们的合影——小学毕业照、运动会、甚至还有我完全不知道她什么时候偷拍的我在田里干活的照片。
"你..."我惊讶得说不出话来。
"卫东,"她认真地看着我,"这些年我一直在等你长大,等你发现我就在这里,从未离开。"
我紧紧抱住了她,闻到她发间淡淡的桂花香。窗外,夏末的知了还在不知疲倦地叫着,而我的心,终于找到了归处。
1993年的春天,我和林芊雪在那棵老槐树下举行了简单的婚礼。
没有豪华酒店,没有迎亲车队,只有赵厂长做证婚人,厂里的工友们用废料焊接了一个心形雕塑当贺礼。林芊雪穿着她母亲当年的红色旗袍,我穿着厂里发的新工作服,胸前别着一朵大红纸花。
"一拜天地!"担任司仪的李大壮扯着嗓子喊。
我和林芊雪面向老槐树深深鞠躬。这棵树见证了我们从两小无猜到今天的喜结连缘,粗糙的树皮上还刻着我们小时候的身高标记。
"二拜高堂!"
我们转向坐在椅子上的双方父母。我父亲病后初愈,眼里含着泪花;林芊雪的父母表情复杂——他们起初反对女儿嫁给一个工人,但在看到我的努力和林芊雪的坚持后,终于勉强同意了。
"夫妻对拜!"
我和林芊雪面对面站着,透过她头纱能看到她亮晶晶的眼睛。我们同时弯腰,额头不小心碰在一起,引得众人哄笑。我的脸发烫,但心里甜得像灌了蜜。
婚礼后的第三天,我就回到了机械厂。赵厂长兑现承诺,提拔我做了技术科副科长,工资涨到了一百八十元。这在当时可是了不起的收入,我终于能慢慢还清父亲的医药费了。
林芊雪依然在镇中学教书,每天下班后还接了几个家教,说是要帮我们早点还清债务。我心疼她太累,于是捡起了木工手艺,利用业余时间做些小家具卖钱。
我们的"家"是工厂分的一间不到二十平米的宿舍。我把废旧机床零件改造成了简易家具——齿轮当桌腿,钢板当桌面,还做了个带锁的柜子专门放林芊雪的书。每天晚上,我在灯下画设计图,她批改学生作业,小小的房间里只有铅笔划过纸面和翻书的沙沙声。
"卫东,你看这个。"结婚三个月后的一天晚上,林芊雪突然递给我一张报纸,"省里要举办工业技术革新大赛,一等奖有五千元奖金呢!"
我接过报纸,眼前一亮。这几个月我一直在琢磨改良厂里的铣床,已经有了初步想法。
"我想试试。"我抬头看她,"但需要买些材料..."
林芊雪二话不说从枕头下拿出一个手绢包:"这是我攒的家教钱,你先用着。"
我紧紧抱住她,闻着她发间淡淡的肥皂香。这个傻姑娘,自己连件新衣服都舍不得买,却全力支持我的梦想。
接下来的一个月,我像着了魔一样。白天在厂里工作,晚上就泡在车间研究改良方案。林芊雪每晚都提着保温桶来给我送饭,有时候等我等到趴在工具箱上睡着。
功夫不负有心人。我的"多功能自动铣床改良装置"不仅获得了省里的一等奖,还引起了省机械厂的注意。颁奖典礼上,一位戴眼镜的领导拍着我的肩膀说:"小伙子,愿不愿意来省城工作?我们正需要你这样的人才。"
回到小镇,我和林芊雪坐在老槐树下商量到深夜。
"去吧。"她靠在我肩上,"这是难得的机会。"
"可你在这里有稳定的工作..."我犹豫道。
"我可以辞职跟你去。"她抬头看我,月光映在她坚定的眼睛里,"卫东,我相信你。就像相信这棵槐树每年春天都会发芽一样。"
就这样,1994年秋天,我们带着全部家当——两个行李箱和一卷铺盖,坐上了去省城的长途汽车。林芊雪在车窗边一直回头望着渐行渐远的小镇,我握紧她的手,在心里发誓一定要混出个样子来。
省城的生活比想象中艰难。我的工资虽然高了些,但房租就去掉大半。林芊雪一时找不到正式工作,只能继续做家教。我们租住在城郊一间潮湿的平房里,冬天墙上会结霜,夏天热得像蒸笼。
但我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白天在工厂如饥似渴地学习新技术,晚上把笔记带回家和林芊雪分享。她虽然不懂机械,却总能提出独到见解。有时候讨论到深夜,我们会突然发现煤油灯都快烧干了。
"卫东,我想去学会计。"一天晚饭时,林芊雪突然说。
我惊讶地抬头:"怎么突然想学这个?"
"我算过了。"她放下筷子,眼睛闪闪发亮,"等你有足够技术和人脉,我们可以自己开个小加工厂。到时候我管账,你管技术,不是很好吗?"
我心头一热。这个看似柔弱的女子,竟已为我们的未来规划得这么远。
"好。"我重重点头,"等我再攒点钱,就送你去培训班。"
1996年,我们的儿子卫小树出生了——名字取自那棵见证我们爱情的老槐树。同年,在林芊雪的鼓励下,我辞去工作,用全部积蓄买了一台二手机床,在我们租的院子里挂出了"东雪精密机械加工"的牌子。
创业的日子苦不堪言。为了省钱,林芊雪月子都没坐满就起来帮我记账、接电话;我常常通宵赶工,手上全是油污和伤口。最困难的时候,我们连续三个月只有咸菜下饭,连奶粉都是赊账买的。
转机出现在一个雨天。一位着急的客户找上门来,说大工厂都不接的小批量急单。我熬了三个通宵,做出了比客户要求精度还高的零件。对方满意得当场加价,还带来了更多客户。
就这样,靠着过硬的技术和诚信经营,我们的"小作坊"渐渐有了起色。三年后,我们搬进了正规厂房,雇了五名工人。林芊雪自学考取了会计证,把公司的账目管理得井井有条。
千禧年到来时,"东雪机械"已经发展到三十多名员工的规模。我们在省城买了套两居室,终于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家。搬新家那天,林芊雪在阳台上种了一棵小槐树苗。
"等小树长大了,我们就能在树下乘凉了。"她笑着说,眼角的细纹在阳光下格外温柔。
2003年,我们公司自主研发的数控机床配件获得国家专利,订单如雪片般飞来。我站在新建的厂房里,看着崭新的设备和忙碌的工人,恍如隔世——十年前,我还是个连三千块钱都还不起的穷小子。
"想什么呢?"林芊雪走到我身边,她已经是个干练的财务总监了,但在我眼里还是那个在老槐树下等我吃饭的姑娘。
"想我们第一次见面讨债的情景。"我笑着搂住她的肩,"林老师,现在我能还得起那三千块钱了,连本带利。"
她捶了我一下:"谁要你的钱。我当初要的是你的人。"
2010年,我们公司上市了。敲钟那天,我特意戴上了当年结婚时的那朵大红纸花——林芊雪一直把它保存在她的宝贝木盒里。记者问我成功的秘诀,我看着台下微笑的妻子,只说了一句:"因为我娶了个好老师。"
如今,我们的儿子小树已经上大学了。每年结婚纪念日,我都会带林芊雪回老家看看那棵老槐树。树干上我们刻的字已经随着树皮变得扭曲模糊,但那份感情,历经岁月却越发清晰坚定。
去年回去时,我们发现老槐树已经被镇政府围起来保护,旁边还立了块牌子:"百年古树,本地文化保护遗产"。我和林芊雪相视一笑,悄悄在牌子背面刻下了我们名字的缩写。
回家的高铁上,林芊雪靠在我肩上睡着了。我轻轻抚摸她已有些花白的头发,想起这二十多年来的点点滴滴——从负债累累到事业有成,从一间宿舍到现在的幸福生活。这一路走来,最大的幸运不是赚了多少钱,而是始终有她相伴。
列车飞驰,窗外的风景飞速后退。我握紧妻子的手,就像当年那辆开往省城的破旧长途车上一样。前方,还有更多美好的风景等着我们一起去见证。
[全文完]


百度分享代码,如果开启HTTPS请参考李洋个人博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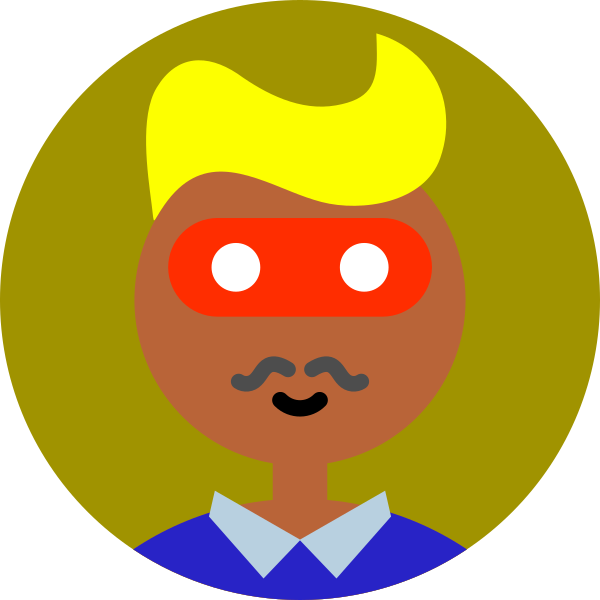









 京公网安备11000000000001号
京公网安备11000000000001号 京ICP备11000001号
京ICP备11000001号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