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您访问的链接即将离开“江门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 是否继续?
继续访问放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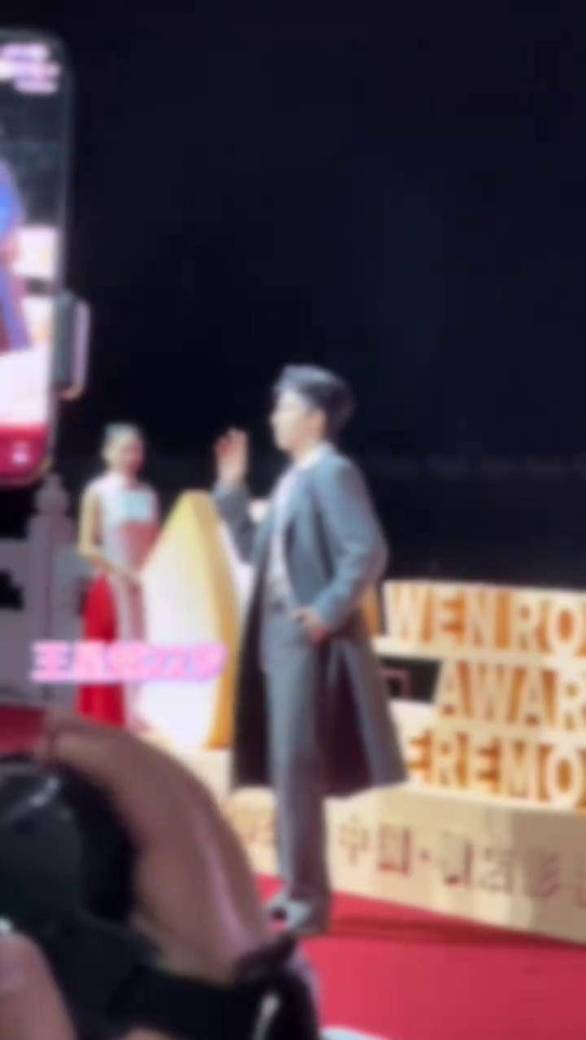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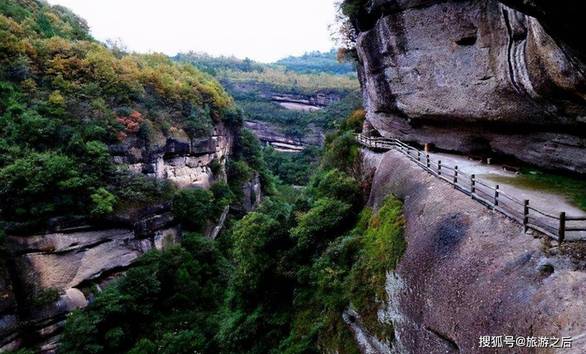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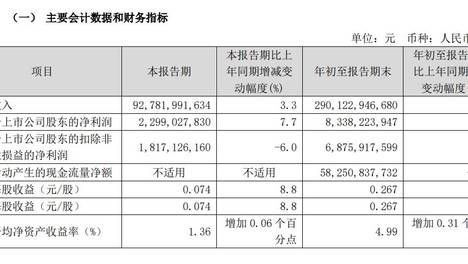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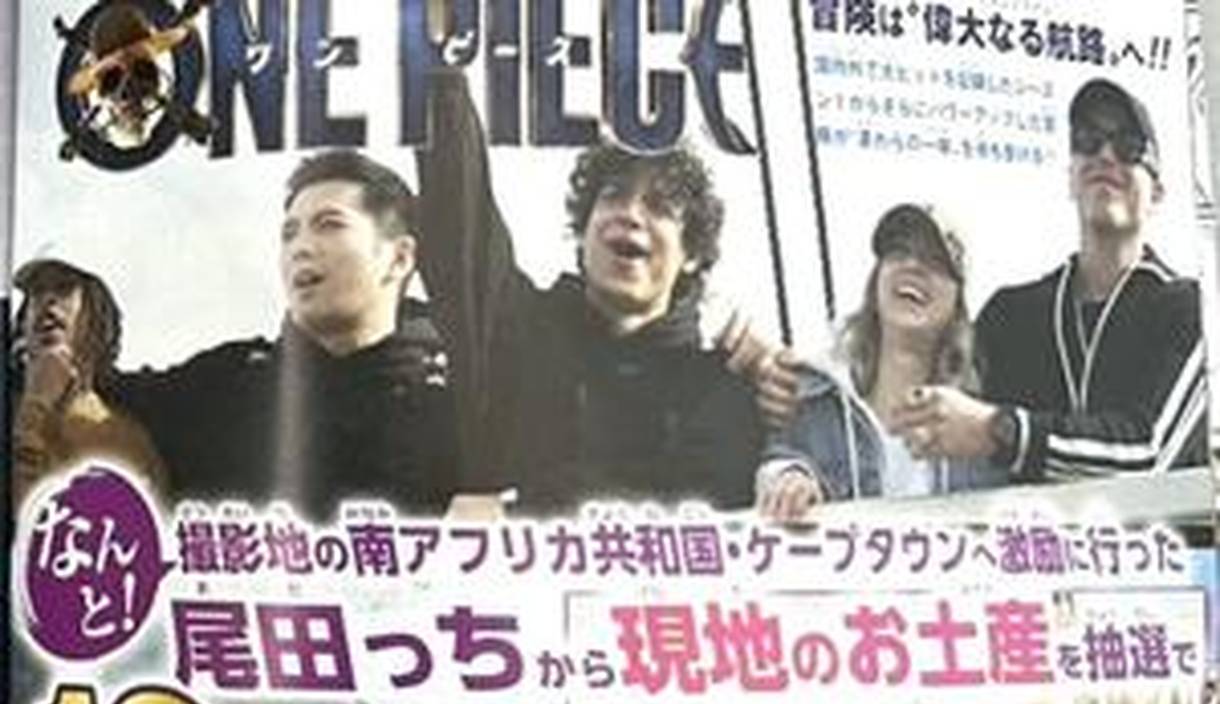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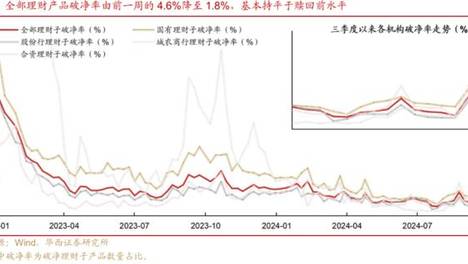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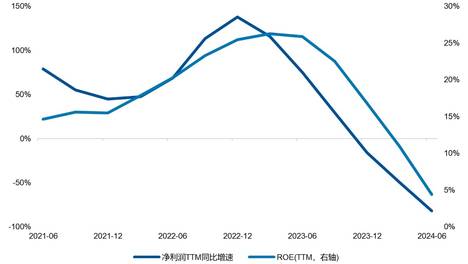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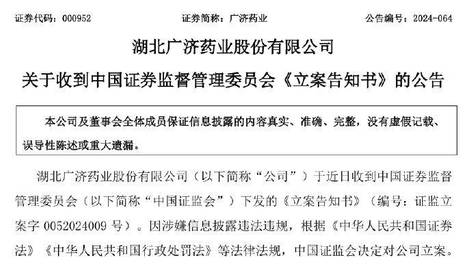







 59655
5965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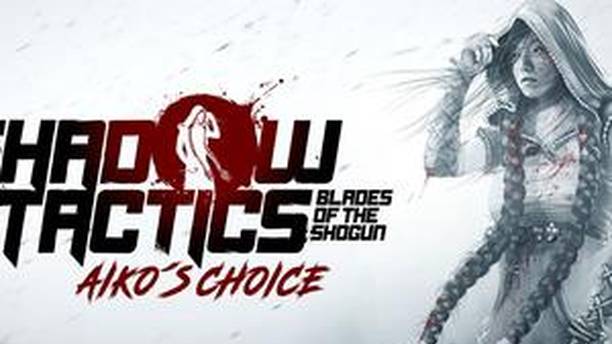 59
2025-07-04 19:14:38
59
2025-07-04 19:14: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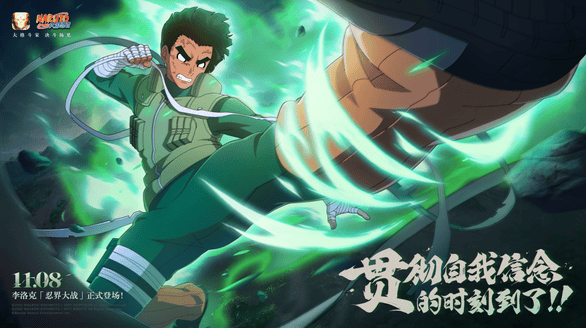


 67698
67698
 25
2025-07-04 19:14:38
25
2025-07-04 19:14:38



 49288
4928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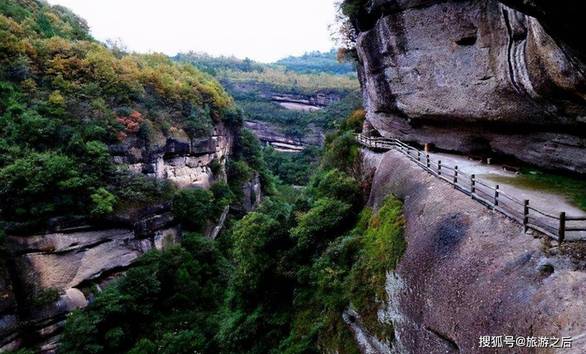 17
2025-07-04 19:14:38
17
2025-07-04 19:14:38



 60990
60990
 26
2025-07-04 19:14:38
26
2025-07-04 19:14:38



 12159
12159
 18
2025-07-04 19:14:38
18
2025-07-04 19:14: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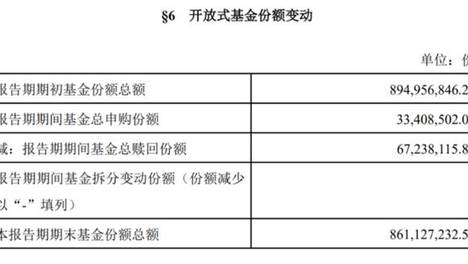 71900
71900
 61
2025-07-04 19:14:38
61
2025-07-04 19:14: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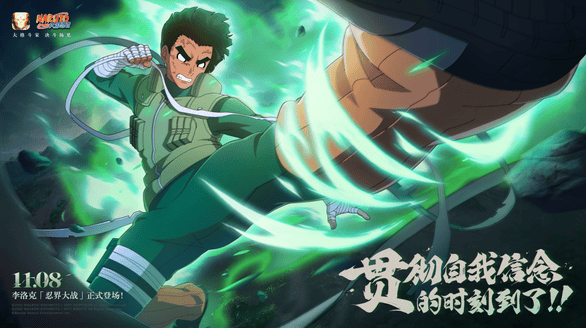

 32082
3208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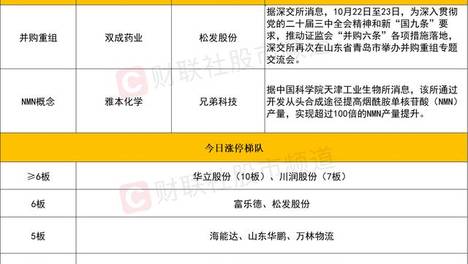 11
2025-07-04 19:14:38
11
2025-07-04 19:14:38



 47045
47045
 42
2025-07-04 19:14:38
42
2025-07-04 19:14:38



 31910
319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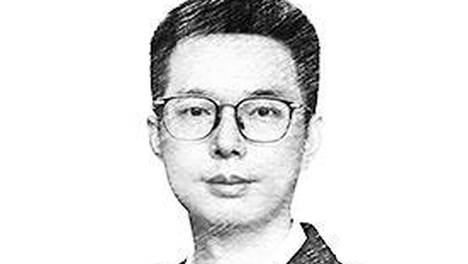 47
2025-07-04 19:14:38
47
2025-07-04 19:14:38



 64524
64524
 67
2025-07-04 19:14:38
67
2025-07-04 19:14:38



 43239
43239
 46
2025-07-04 19:14:38
46
2025-07-04 19:14:38



 28588
28588
 18
2025-07-04 19:14:38
18
2025-07-04 19:14: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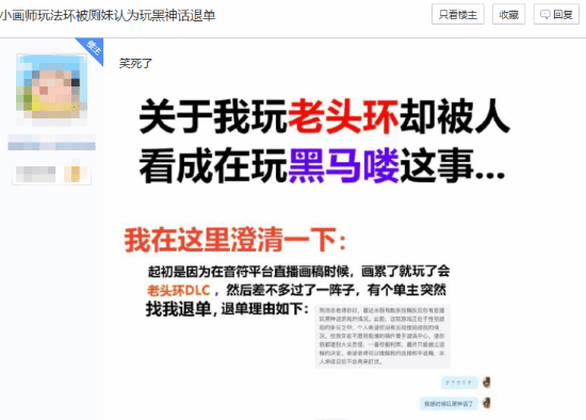 47391
4739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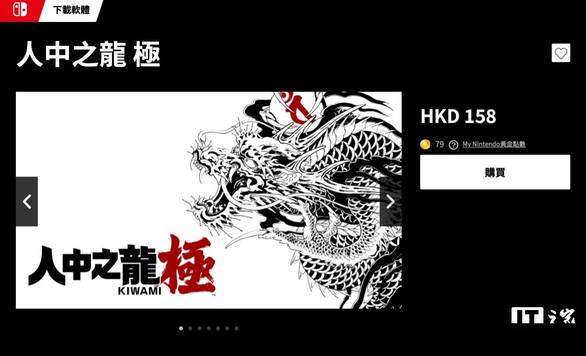 45
2025-07-04 19:14:38
45
2025-07-04 19:14: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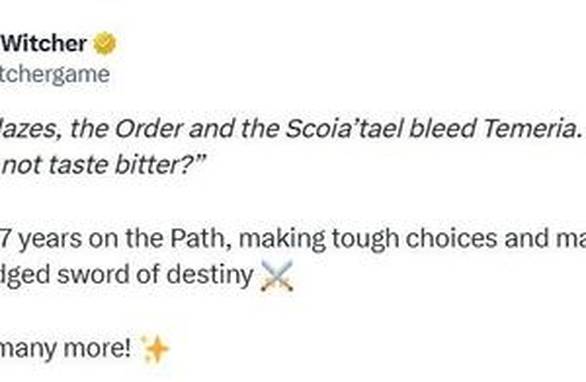 60237
60237
 55
2025-07-04 19:14:38
55
2025-07-04 19:14:38



 43677
43677
 67
2025-07-04 19:14:38
67
2025-07-04 19:14:38



 39030
39030
 86
2025-07-04 19:14:38
86
2025-07-04 19:14: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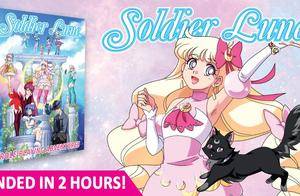 40540
40540
 31
2025-07-04 19:14:38
31
2025-07-04 19:14:38



 85260
85260
 38
2025-07-04 19:14:38
38
2025-07-04 19:14:38



 55684
55684
 32
2025-07-04 19:14:38
32
2025-07-04 19:14: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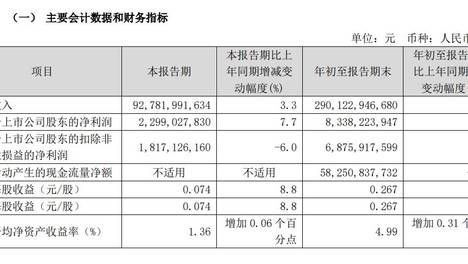 85274
85274
 38
2025-07-04 19:14:38
38
2025-07-04 19:14:38



 19099
1909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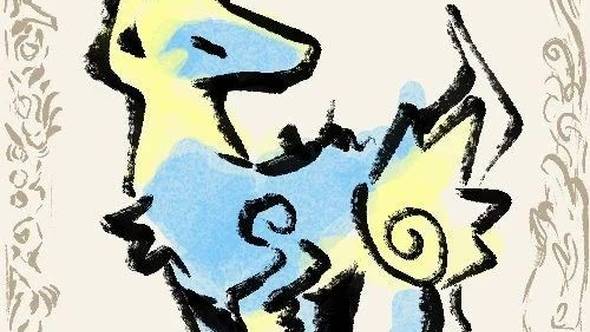 75
2025-07-04 19:14:38
75
2025-07-04 19:14: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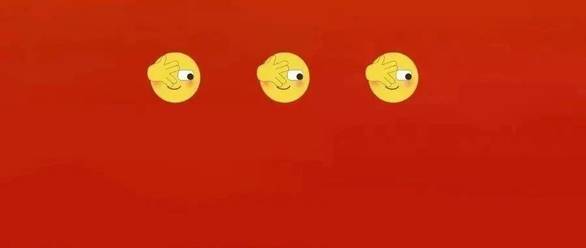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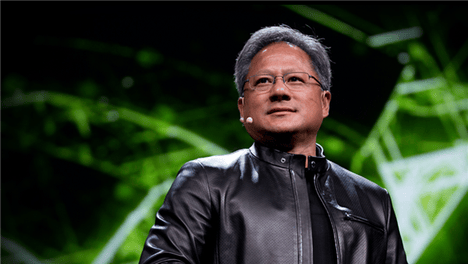

 27352
27352
 32
2025-07-04 19:14:38
32
2025-07-04 19:14:38



 41833
41833
 61
2025-07-04 19:14:38
61
2025-07-04 19:14:38



 82703
82703
 56
2025-07-04 19:14:38
56
2025-07-04 19:14:38



 30890
30890
 73
2025-07-04 19:14:38
73
2025-07-04 19:14:38



 66813
66813
 81
2025-07-04 19:14:38
81
2025-07-04 19:14:38



 11160
111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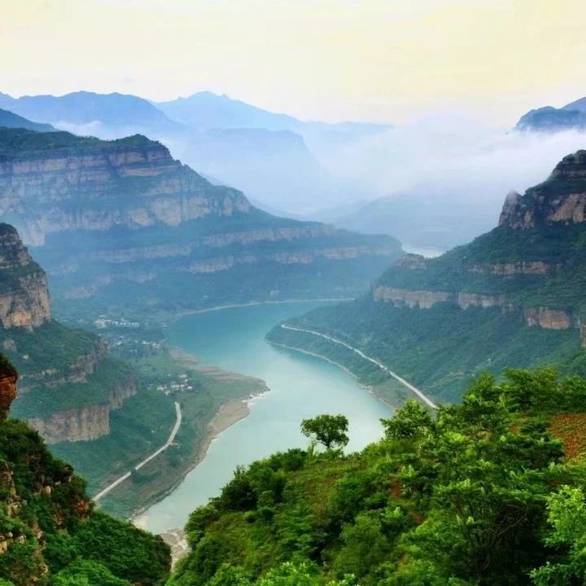 83
2025-07-04 19:14:38
83
2025-07-04 19:14: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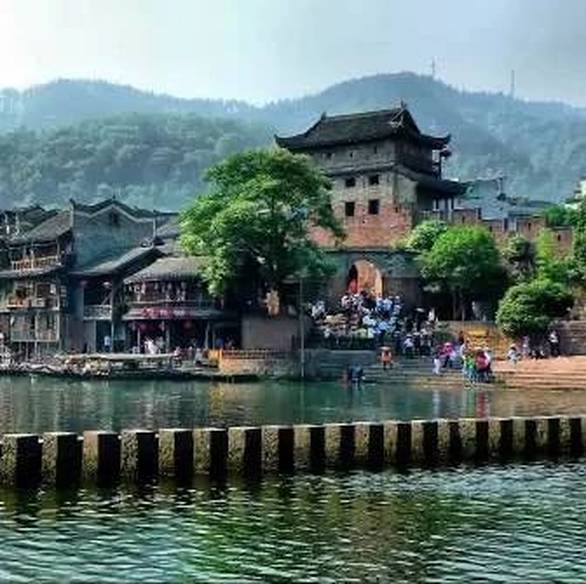 41563
41563
 88
2025-07-04 19:14:38
88
2025-07-04 19:14:38



 21784
21784
 71
2025-07-04 19:14:38
71
2025-07-04 19:14:38



 73251
73251
 39
2025-07-04 19:14:38
39
2025-07-04 19:14: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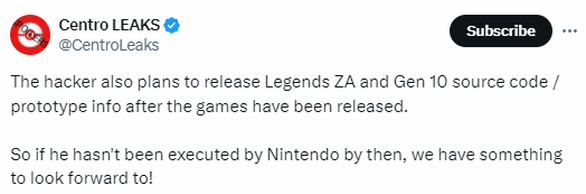

 35016
35016
 79
2025-07-04 19:14:38
79
2025-07-04 19:14: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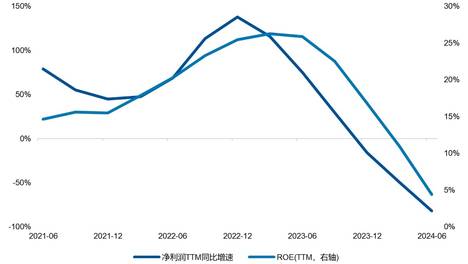

 73689
73689
 24
2025-07-04 19:14:38
24
2025-07-04 19:14:38



 71905
71905
 90
2025-07-04 19:14:38
90
2025-07-04 19:14:38



 18166
18166
 73
2025-07-04 19:14:38
73
2025-07-04 19:14:38



 42786
42786
 28
2025-07-04 19:14:38
28
2025-07-04 19:14: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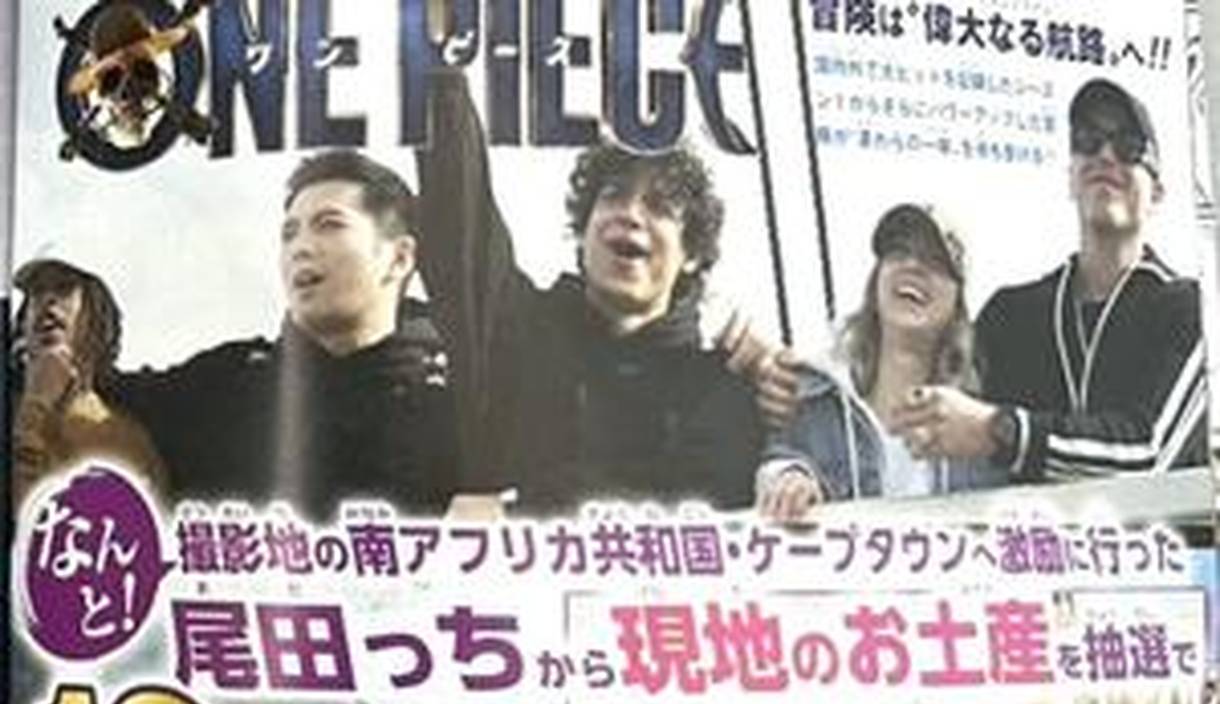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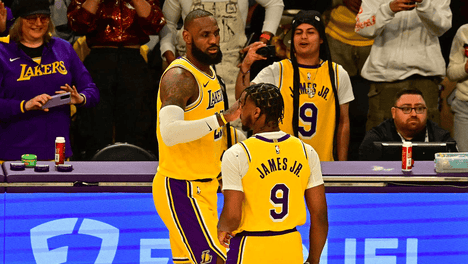 34367
34367
 64
2025-07-04 19:14:38
64
2025-07-04 19:14:38



 35425
35425
 61
2025-07-04 19:14:38
61
2025-07-04 19:14:38



 15590
155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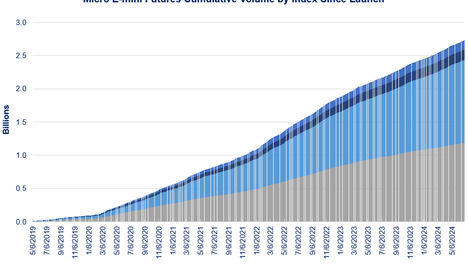 24
2025-07-04 19:14:38
24
2025-07-04 19:14:38



 72674
72674
 51
2025-07-04 19:14:38
51
2025-07-04 19:14:38



 31626
316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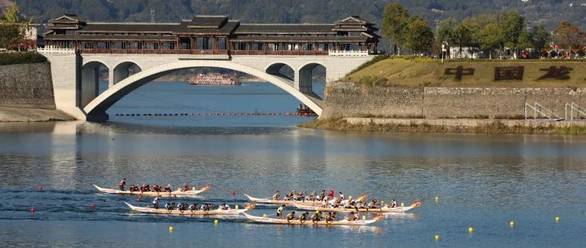 41
2025-07-04 19:14:38
41
2025-07-04 19:14:38



 72910
72910
 38
2025-07-04 19:14:38
38
2025-07-04 19:14:38



 25985
25985
 82
2025-07-04 19:14:38
82
2025-07-04 19:14: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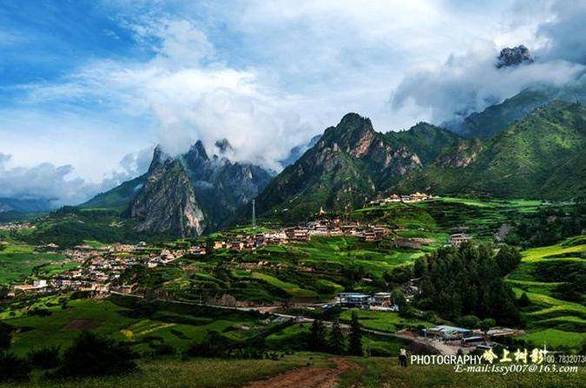

 39282
39282
 86
2025-07-04 19:14:38
86
2025-07-04 19:14: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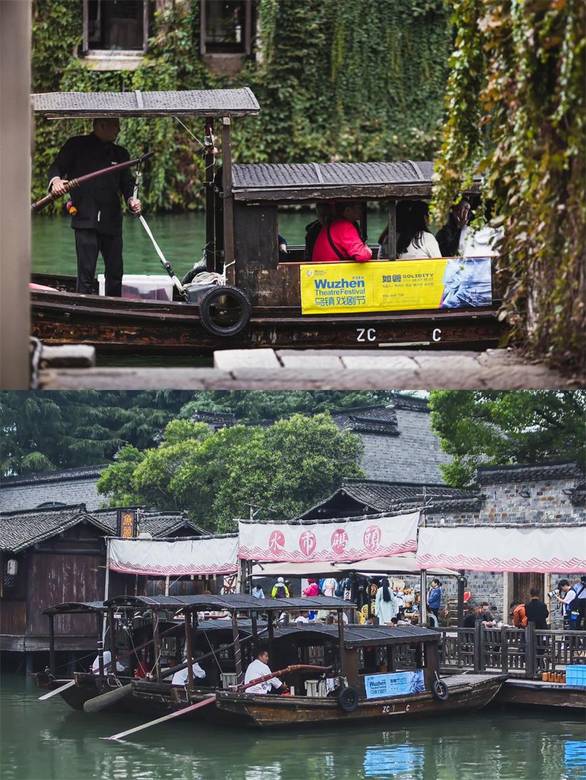

 45944
45944
 12
2025-07-04 19:14:38
12
2025-07-04 19:14:38



 33150
33150
 19
2025-07-04 19:14:38
19
2025-07-04 19:14:38



 37788
37788
 39
2025-07-04 19:14:38
39
2025-07-04 19:14:38



 85345
85345
 30
2025-07-04 19:14:38
30
2025-07-04 19:14:38



 11037
11037
 52
2025-07-04 19:14:38
52
2025-07-04 19:14: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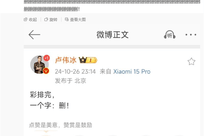


 40596
40596
 47
2025-07-04 19:14:38
47
2025-07-04 19:14: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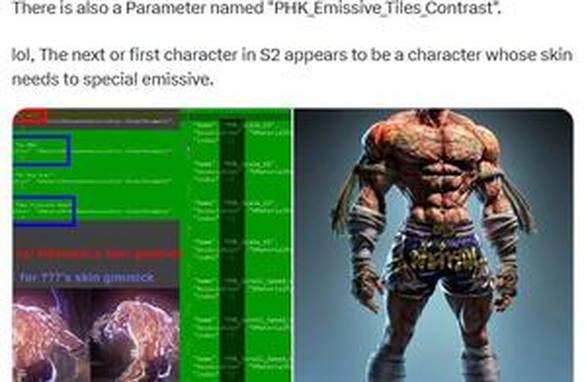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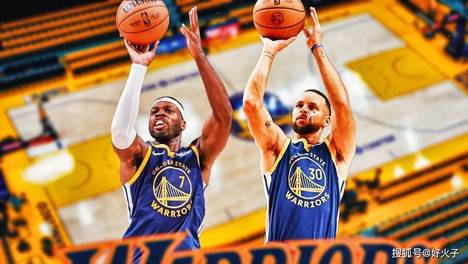

 58457
58457
 69
2025-07-04 19:14:38
69
2025-07-04 19:14:38



 22353
22353
 10
2025-07-04 19:14:38
10
2025-07-04 19:14: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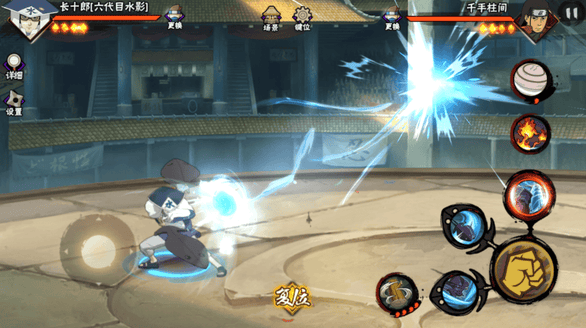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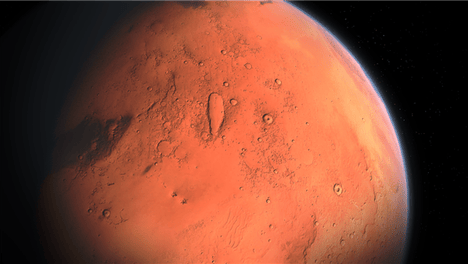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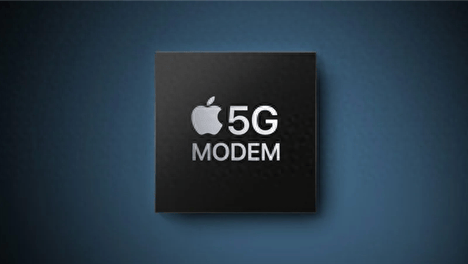 70699
70699
 59
2025-07-04 19:14:38
59
2025-07-04 19:14:38



 31869
3186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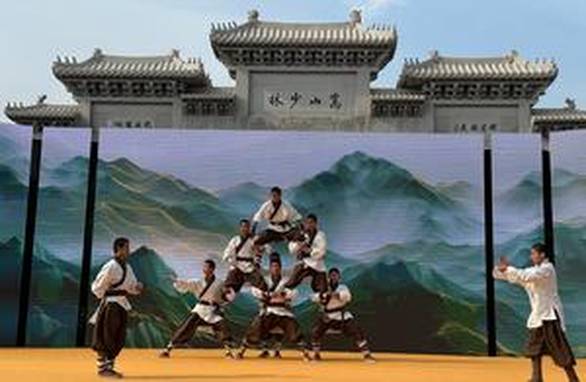 18
2025-07-04 19:14:38
18
2025-07-04 19:14:38



 73309
73309
 44
2025-07-04 19:14:38
44
2025-07-04 19:14:38
| 注意这个林彪式的人物,为儿子上位,什么都敢。zhu yi zhe ge lin biao shi de ren wu ,wei er zi shang wei ,shen me dou gan 。 | 38天天前 |
| 洪森就是一个无耻无赖之徒 | |
| 连大师赛都没有……还大满贯?lian da shi sai dou mei you ……hai da man guan ? | 79天天前 |
| 好 | |
| 这不叫冷门zhe bu jiao leng men | 25天天前 |
| 还好有佩佩姐作伴,否则是被淘汰的最高种子了 | |
| 最水五号种子,职业生涯1000赛冠军没拿过,更别说大满贯了,拿得出手的就一个500赛冠军。zui shui wu hao zhong zi ,zhi ye sheng ya 1000sai guan jun mei na guo ,geng bie shuo da man guan le ,na de chu shou de jiu yi ge 500sai guan jun 。 | 61天天前 |
| 水平就这样 | |
| 非常好fei chang hao | 58天天前 |
| 一轮游?吃便吧! | |
| 对,太正常了。dui ,tai zheng chang le 。 | 46天天前 |
| 郑钦文打球太追求一发的速度了, S求排名第一是没有屁用的。要降低一点速度,追求一发的成功率。看她打球感觉就是用一发的s求和2发球与别人在拼。动脑筋算草适当降低速度,得分会增加很多。 | |
| 打的不是一般的差劲da de bu shi yi ban de cha jin | 71天天前 |
| 世界排名第五就是他妈的笑话 | |
| 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可依然牛气冲天!不行就是不行!wen ti yi zhi mei you jie jue ,ke yi ran niu qi chong tian !bu xing jiu shi bu xing ! | 21天天前 |
| 就是个笑话,还想翻这山那山,谁知到处是山 | |
| 郑钦文又是一轮游,打脸媒体炒作和吹捧,郑钦文自己说很适合草地的。实际上打法确实不适合草地,对方击球那么靠近底线,还强行变线,回球都飞得很离谱。郑钦文热身那么长时间,都没调整适应过来场地,以后别再吹牛啦,更别提夺冠。zheng qin wen you shi yi lun you ,da lian mei ti chao zuo he chui peng ,zheng qin wen zi ji shuo hen shi he cao di de 。shi ji shang da fa que shi bu shi he cao di ,dui fang ji qiu na me kao jin di xian ,hai qiang xing bian xian ,hui qiu dou fei de hen li pu 。zheng qin wen re shen na me chang shi jian ,dou mei tiao zheng shi ying guo lai chang di ,yi hou bie zai chui niu la ,geng bie ti duo guan 。 | 49天天前 |
| [狗头][狗头] 相比湖人 真是[暗中观察] | |
| 如果不签到芬尼,卡佩拉,入季后赛无望,现在可能入到对付附加赛。ru guo bu qian dao fen ni ,ka pei la ,ru ji hou sai wu wang ,xian zai ke neng ru dao dui fu fu jia sai 。 | 62天天前 |
| 看来森森和白沫要散了 一个拿1500以上一个1000以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