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您访问的链接即将离开“江门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 是否继续?
继续访问放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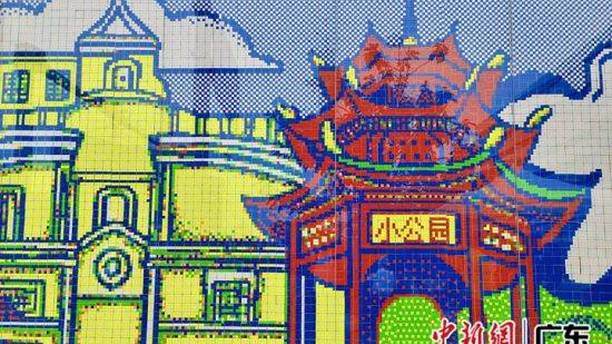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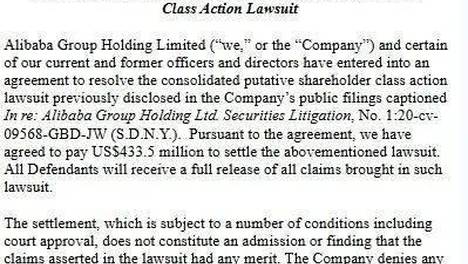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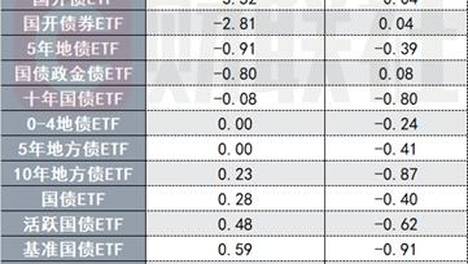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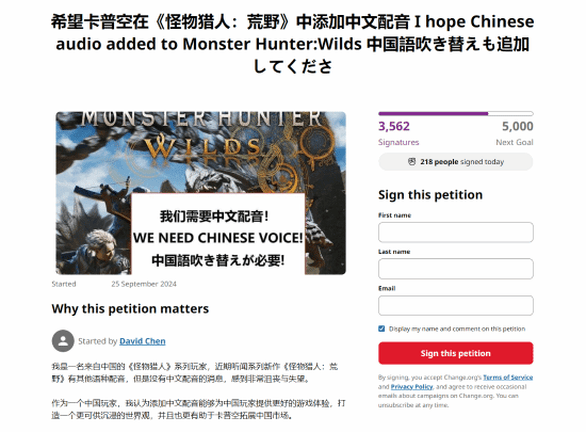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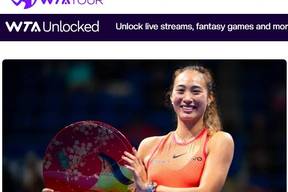 10467
10467
 42
2025-08-20 17:09:16
42
2025-08-20 17:09: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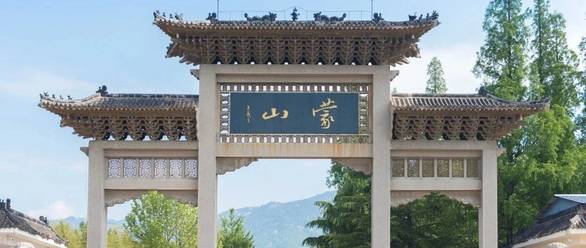 22010
22010
 60
2025-08-20 17:09:16
60
2025-08-20 17:09: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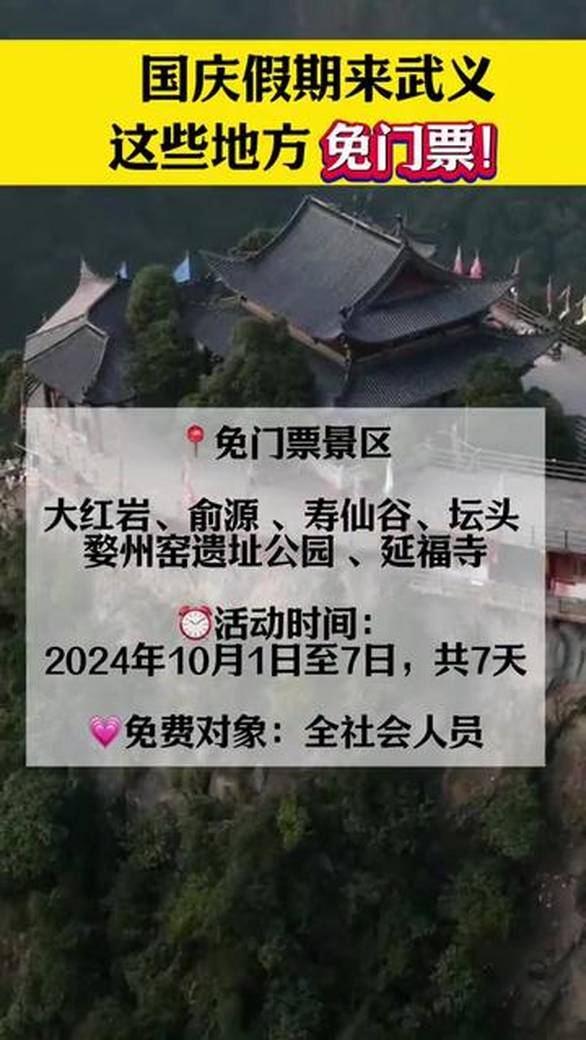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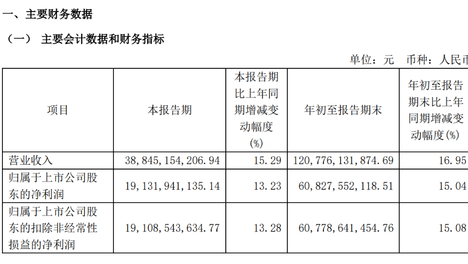 57323
57323
 88
2025-08-20 17:09:16
88
2025-08-20 17:09: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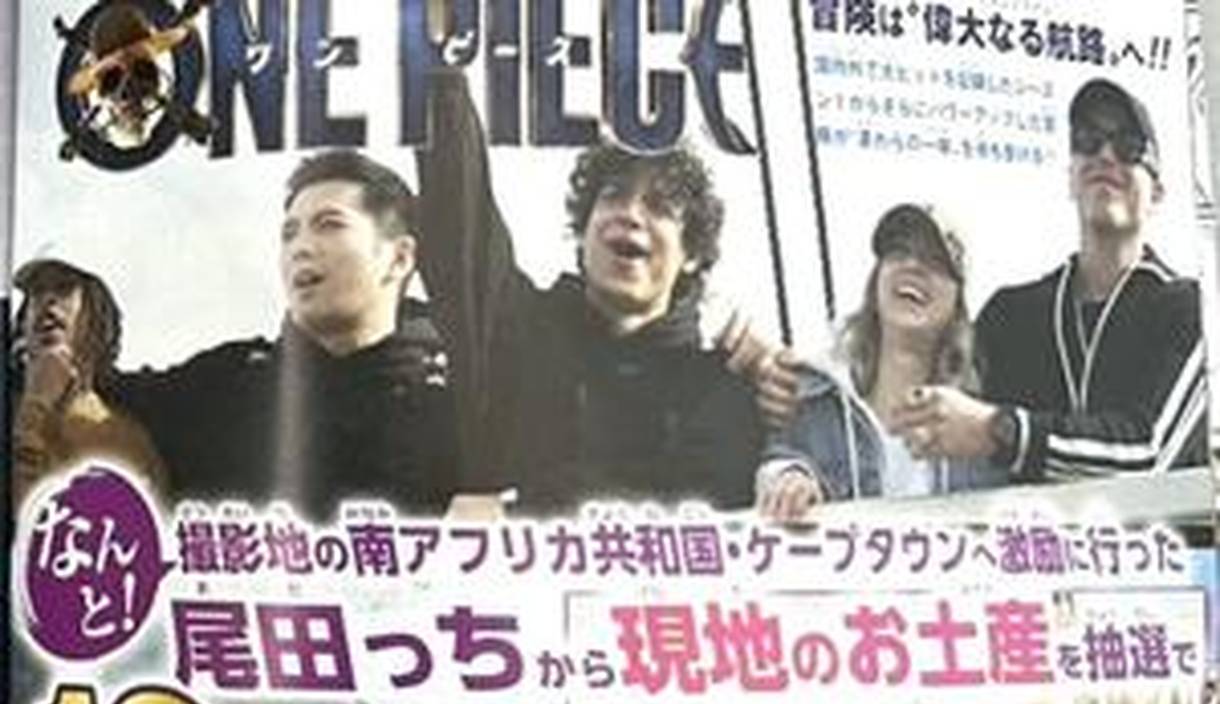 26720
26720
 36
2025-08-20 17:09:16
36
2025-08-20 17:09:16



 11689
11689
 77
2025-08-20 17:09:16
77
2025-08-20 17:09:16



 17390
17390
 81
2025-08-20 17:09:16
81
2025-08-20 17:09: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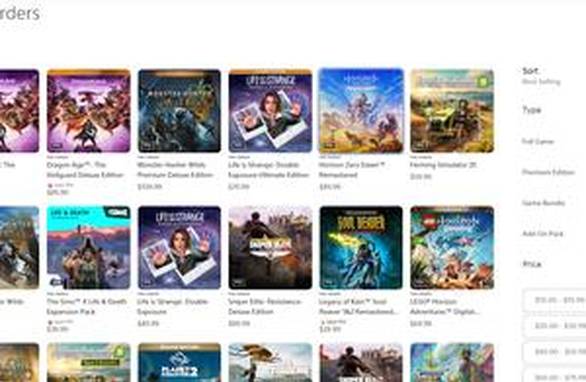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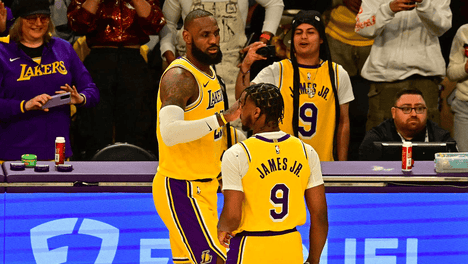 77590
77590
 33
2025-08-20 17:09:16
33
2025-08-20 17:09:16



 84064
84064
 55
2025-08-20 17:09:16
55
2025-08-20 17:09:16



 68786
68786
 34
2025-08-20 17:09:16
34
2025-08-20 17:09:16



 89765
89765
 69
2025-08-20 17:09:16
69
2025-08-20 17:09:16



 83994
83994
 62
2025-08-20 17:09:16
62
2025-08-20 17:09:16



 71426
71426
 16
2025-08-20 17:09:16
16
2025-08-20 17:09: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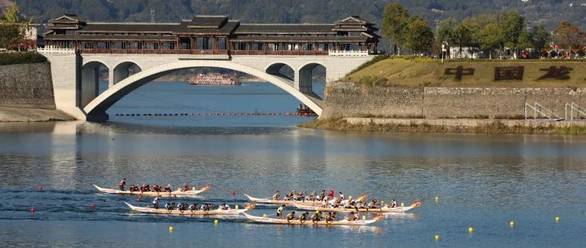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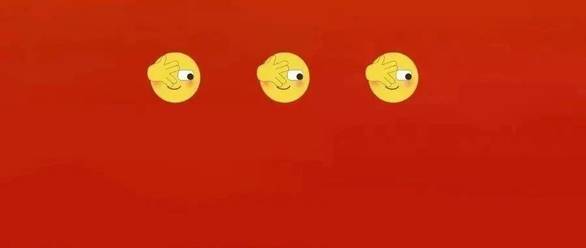

 12241
1224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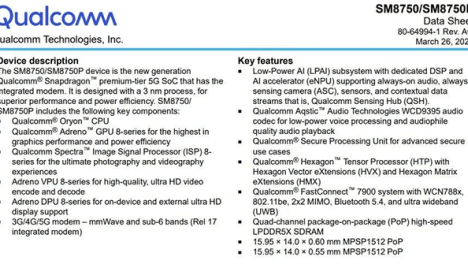 30
2025-08-20 17:09:16
30
2025-08-20 17:09:16



 87472
87472
 61
2025-08-20 17:09:16
61
2025-08-20 17:09: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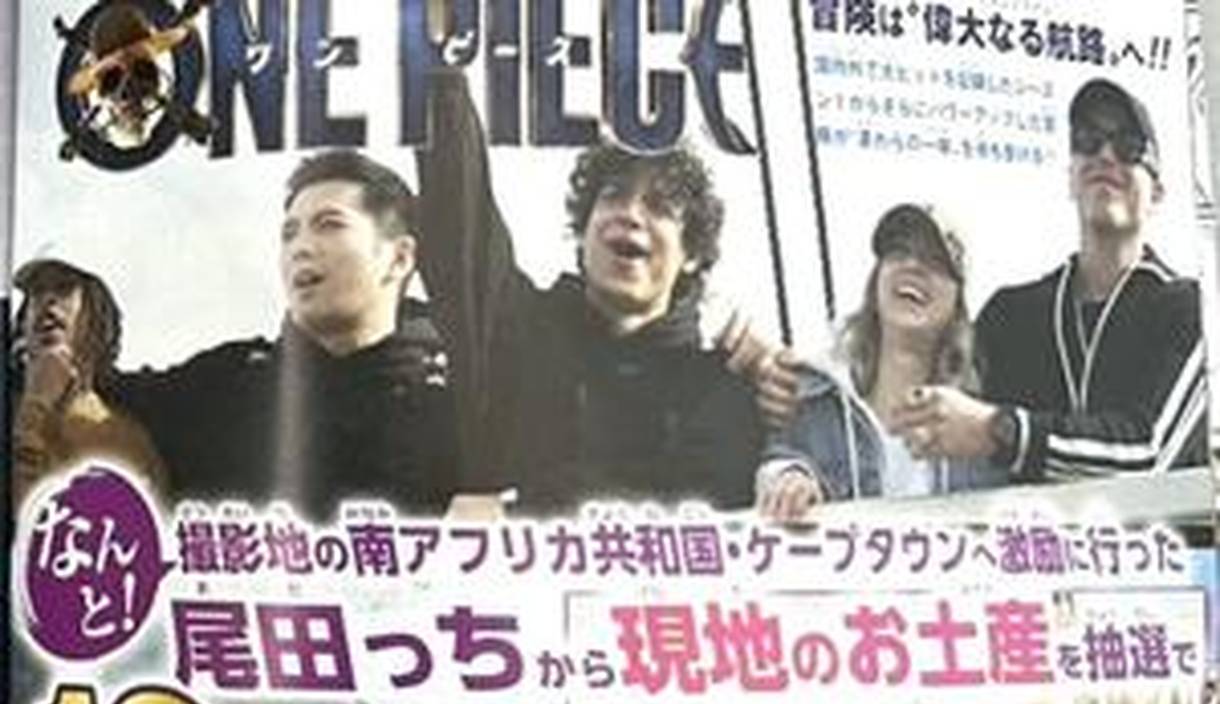

 14502
14502
 90
2025-08-20 17:09:16
90
2025-08-20 17:09:16



 54814
54814
 86
2025-08-20 17:09:16
86
2025-08-20 17:09: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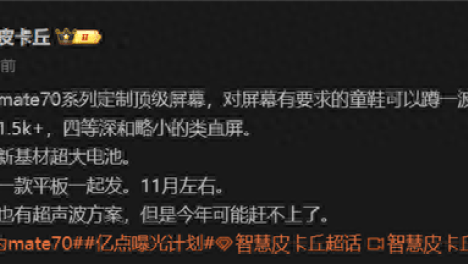 40813
408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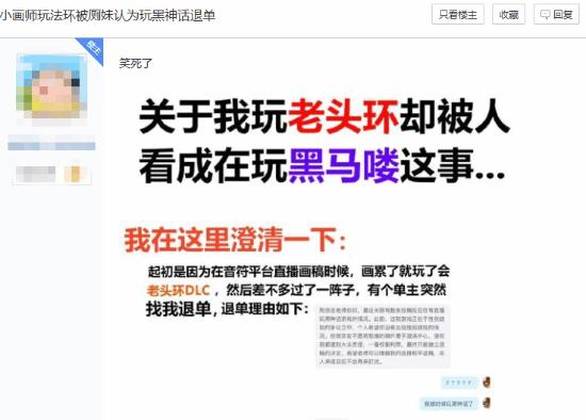 54
2025-08-20 17:09:16
54
2025-08-20 17:09: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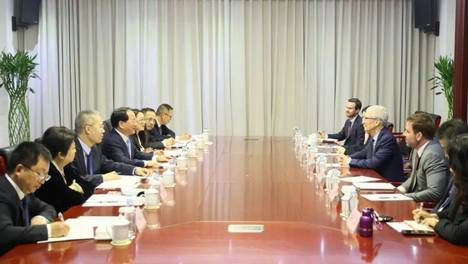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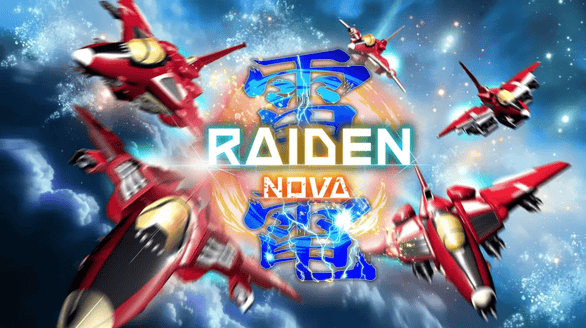

 69241
69241
 16
2025-08-20 17:09:16
16
2025-08-20 17:09: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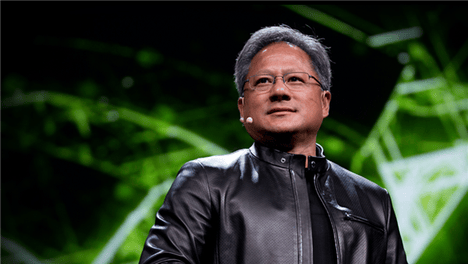


 84326
84326
 85
2025-08-20 17:09:16
85
2025-08-20 17:09: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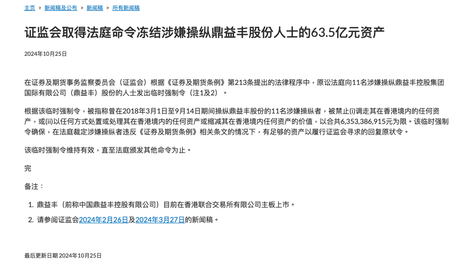


 14110
141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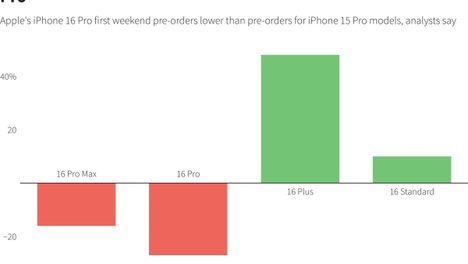 17
2025-08-20 17:09:16
17
2025-08-20 17:09:16



 83750
83750
 62
2025-08-20 17:09:16
62
2025-08-20 17:09: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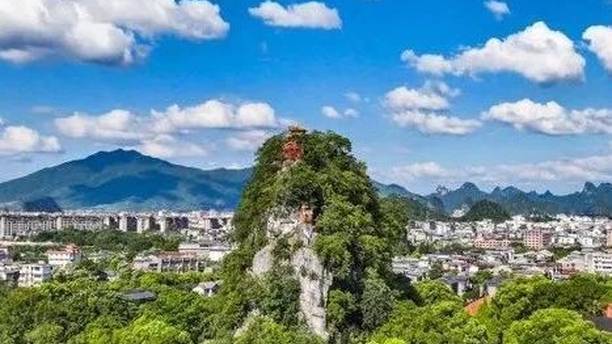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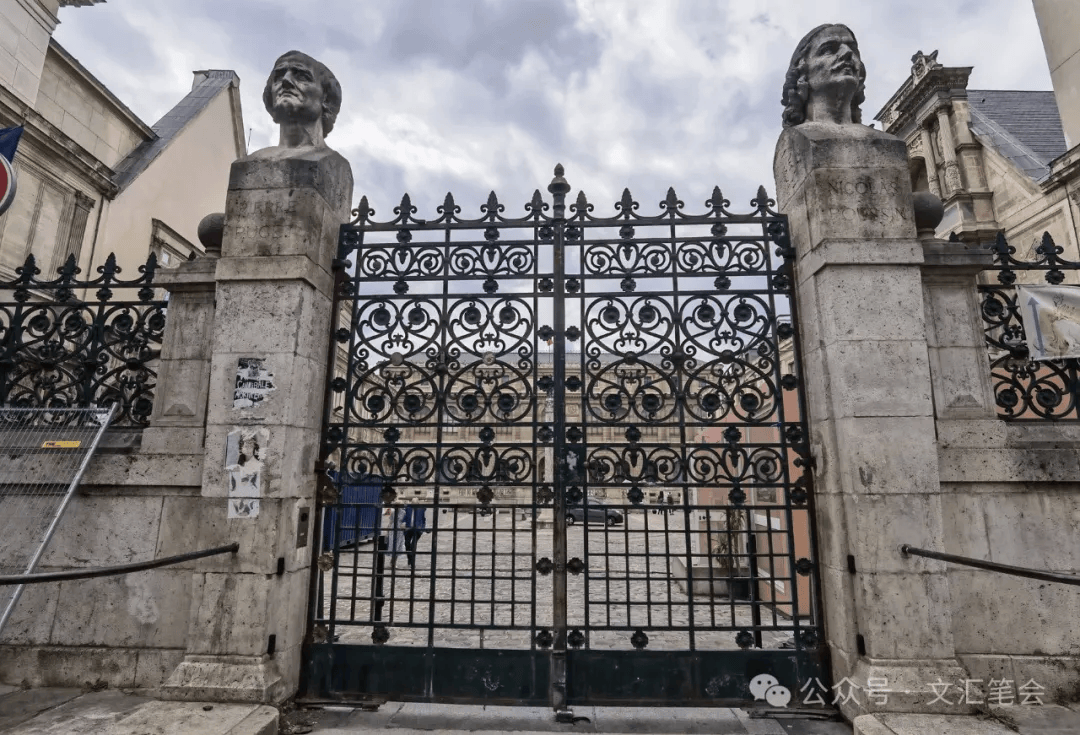 35089
35089
 15
2025-08-20 17:09:16
15
2025-08-20 17:09:16



 51778
51778
 58
2025-08-20 17:09:16
58
2025-08-20 17:09: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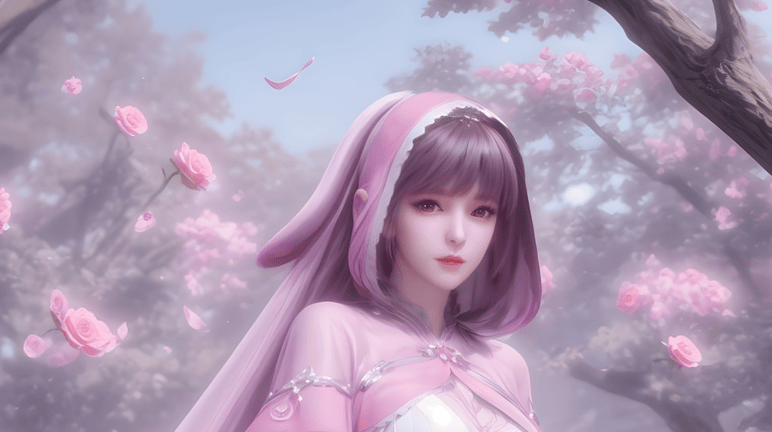 22474
22474
 23
2025-08-20 17:09:16
23
2025-08-20 17:09: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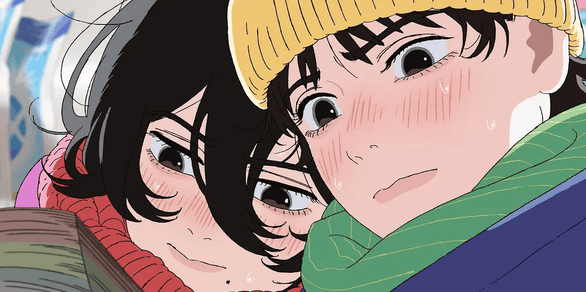

 63186
63186
 23
2025-08-20 17:09:16
23
2025-08-20 17:09:16



 64303
64303
 65
2025-08-20 17:09:16
65
2025-08-20 17:09: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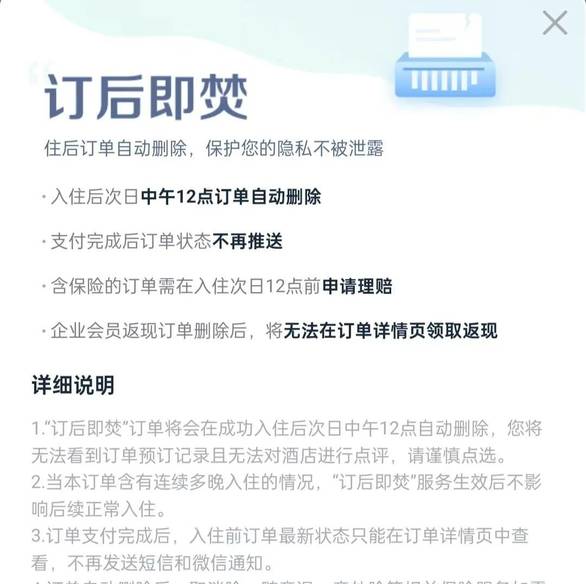

 11211
112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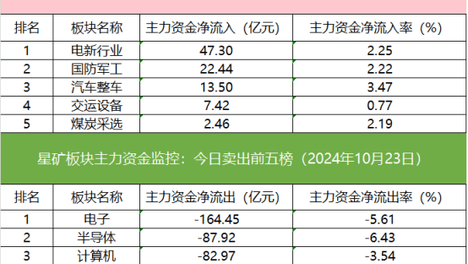 82
2025-08-20 17:09:16
82
2025-08-20 17:09:16



 56481
56481
 35
2025-08-20 17:09:16
35
2025-08-20 17:09:16



 61784
61784
 90
2025-08-20 17:09:16
90
2025-08-20 17:09: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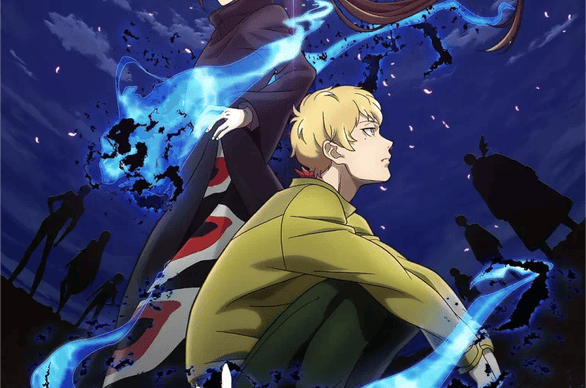


 57589
57589
 37
2025-08-20 17:09:16
37
2025-08-20 17:09:16



 53815
53815
 48
2025-08-20 17:09:16
48
2025-08-20 17:09: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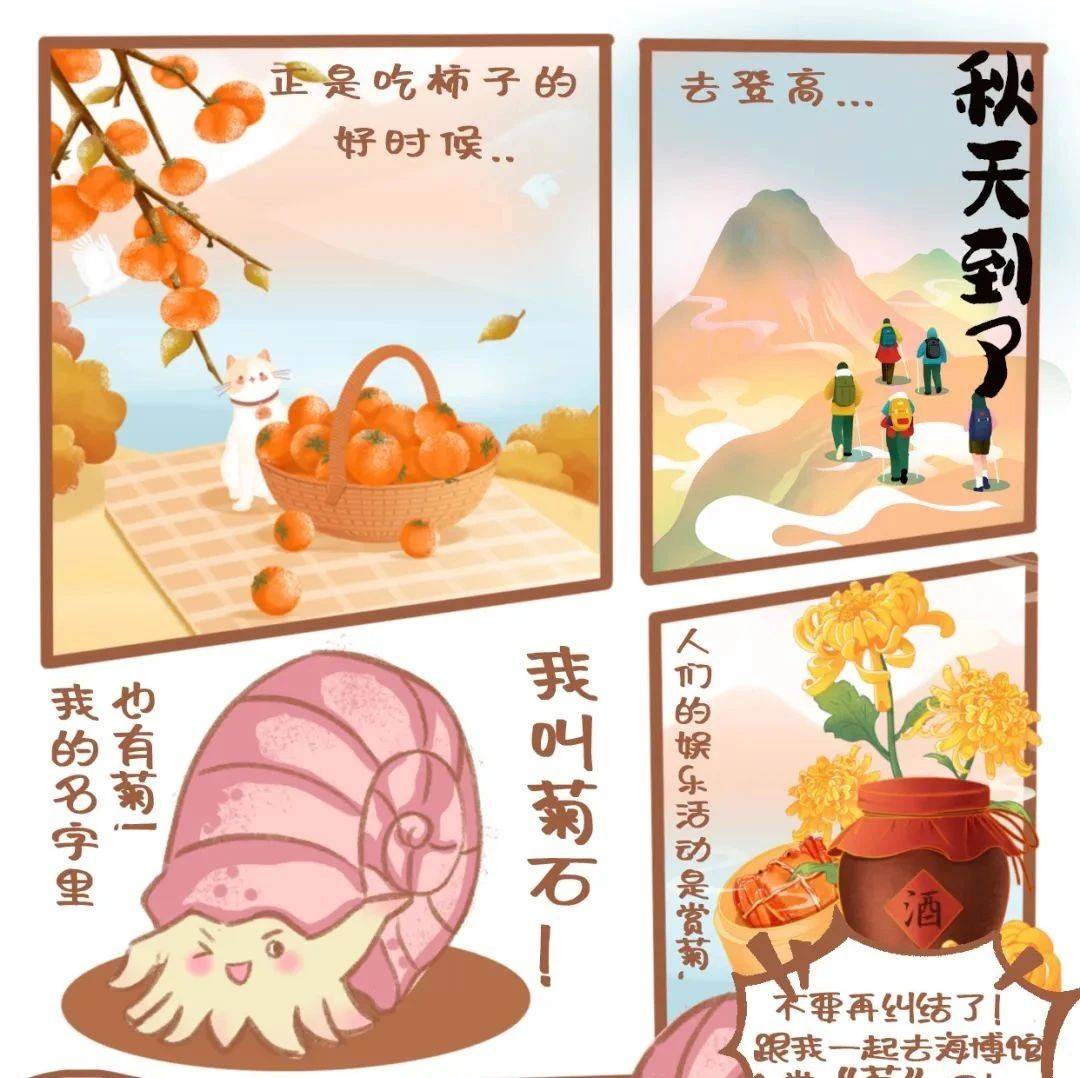

 66137
66137
 25
2025-08-20 17:09:16
25
2025-08-20 17:09:16



 46252
46252
 69
2025-08-20 17:09:16
69
2025-08-20 17:09: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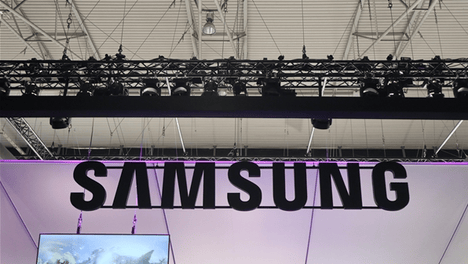 51416
51416
 57
2025-08-20 17:09:16
57
2025-08-20 17:09:16



 88911
88911
 40
2025-08-20 17:09:16
40
2025-08-20 17:09: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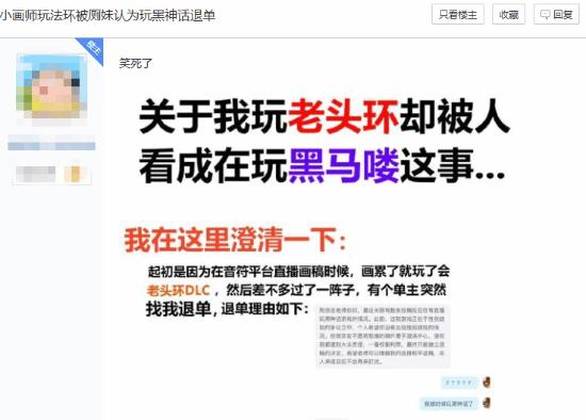


 33263
33263
 14
2025-08-20 17:09:16
14
2025-08-20 17:09:16



 34836
34836
 75
2025-08-20 17:09:16
75
2025-08-20 17:09:16



 26571
26571
 68
2025-08-20 17:09:16
68
2025-08-20 17:09: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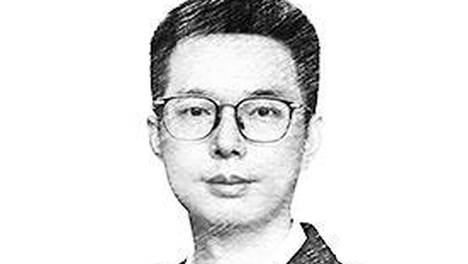 75324
75324
 65
2025-08-20 17:09:16
65
2025-08-20 17:09:16



 78367
78367
 10
2025-08-20 17:09:16
10
2025-08-20 17:09: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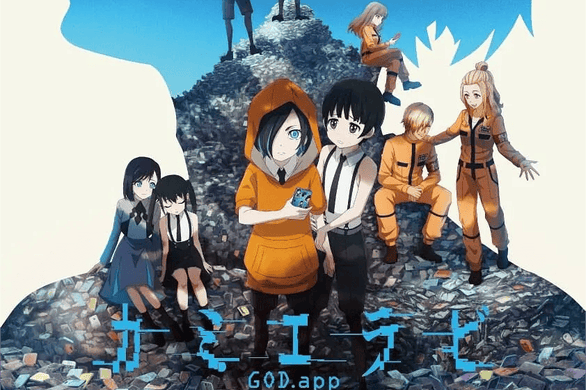

 56420
56420
 40
2025-08-20 17:09:16
40
2025-08-20 17:09:16



 13914
139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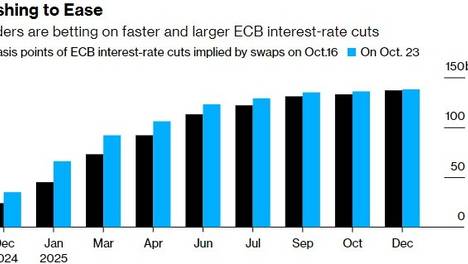 68
2025-08-20 17:09:16
68
2025-08-20 17:09:16



 70718
70718
 39
2025-08-20 17:09:16
39
2025-08-20 17:09: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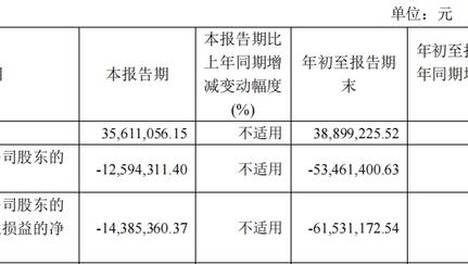

 45385
45385
 34
2025-08-20 17:09:16
34
2025-08-20 17:09:16



 80994
80994
 48
2025-08-20 17:09:16
48
2025-08-20 17:09: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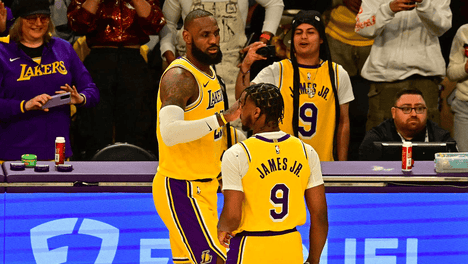 53396
53396
 28
2025-08-20 17:09:16
28
2025-08-20 17:09:16



 40900
40900
 39
2025-08-20 17:09:16
39
2025-08-20 17:09:16



 54755
54755
 26
2025-08-20 17:09:16
26
2025-08-20 17:09: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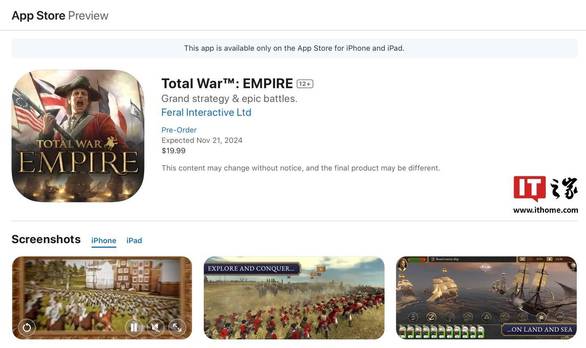


 57123
571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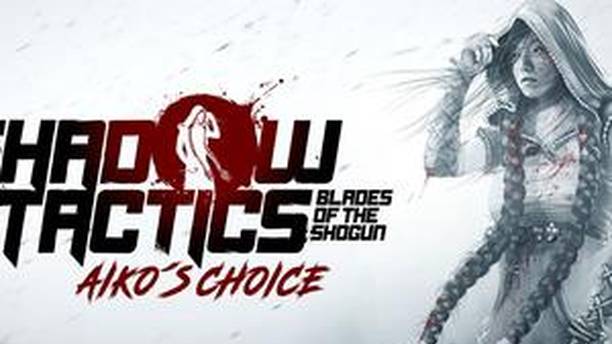 58
2025-08-20 17:09:16
58
2025-08-20 17:09: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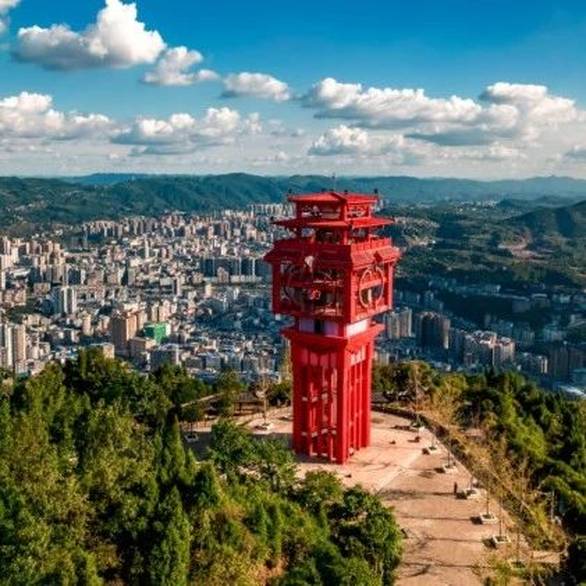 37422
37422
 43
2025-08-20 17:09:16
43
2025-08-20 17:09:16



 37640
37640
 18
2025-08-20 17:09:16
18
2025-08-20 17:09:16



 52161
52161
 36
2025-08-20 17:09:16
36
2025-08-20 17:09: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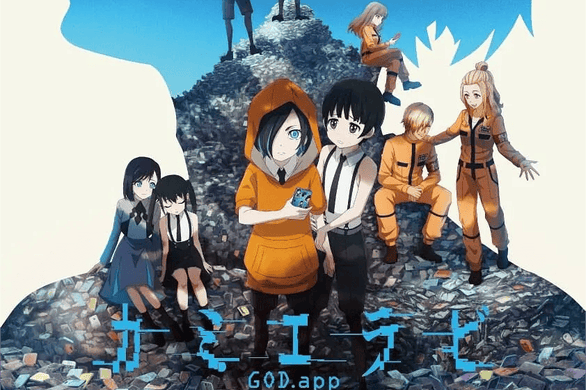 70948
70948
 20
2025-08-20 17:09:16
20
2025-08-20 17:09: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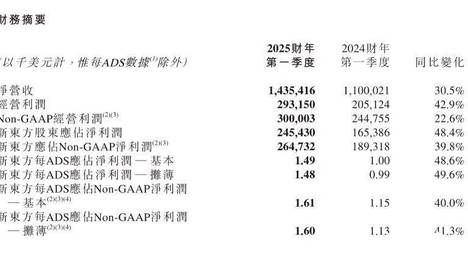

 81570
81570
 68
2025-08-20 17:09:16
68
2025-08-20 17:09:16
| 西藏各族儿女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xi zang ge zu er nv xiang shi liu zi yi yang jin jin bao zai yi qi | 88天天前 |
| 永远跟党走,创造更美好生活 | |
| 到时打脸时候你是跪下还是自杀?未战先怯,打起仗来你这种人就是汉奸走狗!dao shi da lian shi hou ni shi gui xia hai shi zi sha ?wei zhan xian qie ,da qi zhang lai ni zhe zhong ren jiu shi han jian zou gou ! | 29天天前 |
| 这批男篮球员打的有血性,值得期待 | |
| 十年来,中国男篮获得两个亚洲冠军,一个亚洲亚军,一个亚洲第8名,请看:2015年男篮亚洲杯,主教练宫鲁鸣率队全胜夺得亚洲冠军。2018年亚运会,主教练李楠率队全胜夺得男篮亚洲冠军。2022年亚洲杯主教练杜锋率队夺得亚洲第8名(耻辱)。2025年男篮亚洲杯,主教练郭士强率队夺得亚洲亚军。shi nian lai ,zhong guo nan lan huo de liang ge ya zhou guan jun ,yi ge ya zhou ya jun ,yi ge ya zhou di 8ming ,qing kan :2015nian nan lan ya zhou bei ,zhu jiao lian gong lu ming lv dui quan sheng duo de ya zhou guan jun 。2018nian ya yun hui ,zhu jiao lian li nan lv dui quan sheng duo de nan lan ya zhou guan jun 。2022nian ya zhou bei zhu jiao lian du feng lv dui duo de ya zhou di 8ming (chi ru )。2025nian nan lan ya zhou bei ,zhu jiao lian guo shi qiang lv dui duo de ya zhou ya jun 。 | 32天天前 |
| 爷是你野爹,傻狗 | |
| 把这厮抓起来ba zhe si zhua qi lai | 41天天前 |
| 就是,不像周琦、赵继伟等人只能内战,外战就拉希摆烂!不敢冲击内线,怕对抗,动不动就因伤躺平! | |
| 跪久了起不来了gui jiu le qi bu lai le | 41天天前 |
| 这个奴才跪久了起不来了 | |
| 点赞dian zan | 53天天前 |
| 相比之下,男篮在天男足在地! | |
| 排面pai mian | 60天天前 |
| 篮协及球员所属俱乐部除了给于宣传鼓励也应该物质重赏全体班子!让所有中国篮球人知道国家队才是最大金子号舞台,离开这个平台你什么也不是,很快被篮球忘记! | |
| 男篮是非常棒的。可是新闻联播有人看吗?哪来的排面!nan lan shi fei chang bang de 。ke shi xin wen lian bo you ren kan ma ?na lai de pai mian ! | 71天天前 |
| 别再吹了,我可以断定,这只男篮还是进不去奥运会,等着再别打脸!亚洲杯只是各国考察新人的一项比赛而已,还真把自己当回事了 | |
| 应该!血性将土!ying gai !xue xing jiang tu ! | 34天天前 |
| 斯基顽强抵抗防守未果,愤而辞职,换酋,事成 | |
| 猪狗不如的东西zhu gou bu ru de dong xi | 57天天前 |
| 怎么感觉是二战慕尼黑会议的翻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