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您访问的链接即将离开“江门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 是否继续?
继续访问放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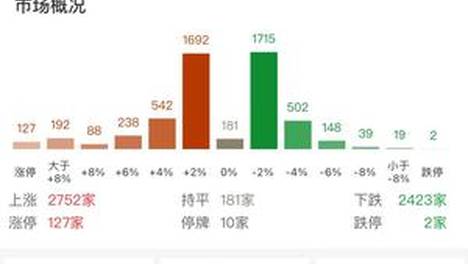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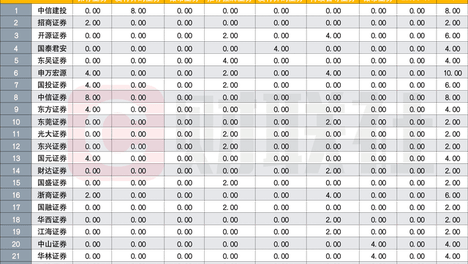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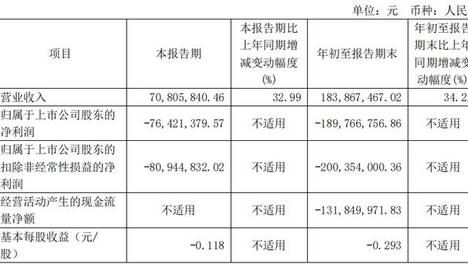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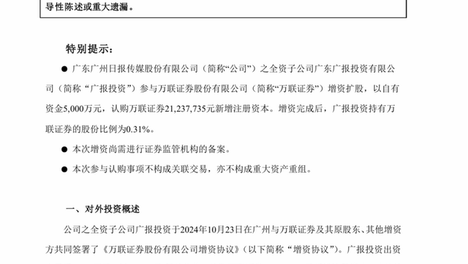



 40266
40266
 82
2025-08-22 00:21:43
82
2025-08-22 00:21:43



 44747
44747
 30
2025-08-22 00:21:43
30
2025-08-22 00:21:4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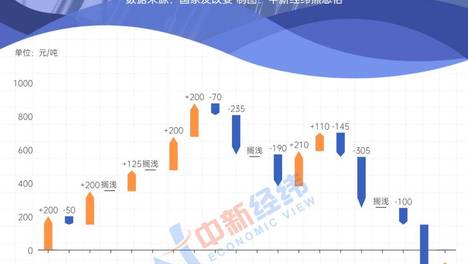 59894
5989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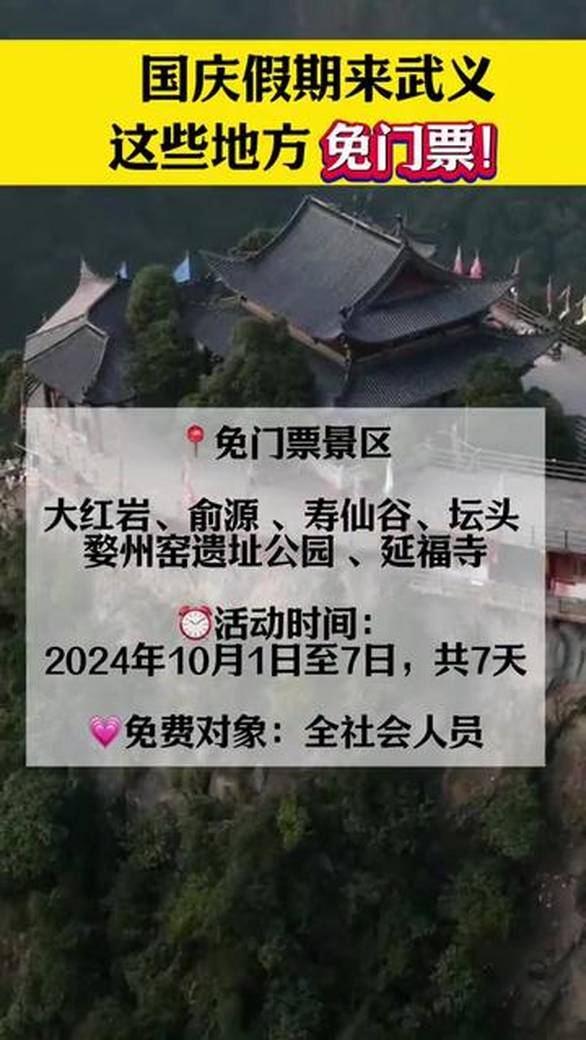 52
2025-08-22 00:21:43
52
2025-08-22 00:21:4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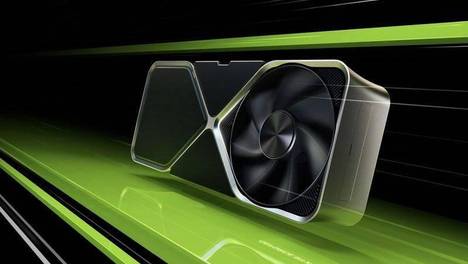

 88792
88792
 72
2025-08-22 00:21:43
72
2025-08-22 00:21:43



 71912
71912
 10
2025-08-22 00:21:43
10
2025-08-22 00:21:43



 80465
80465
 17
2025-08-22 00:21:43
17
2025-08-22 00:21:4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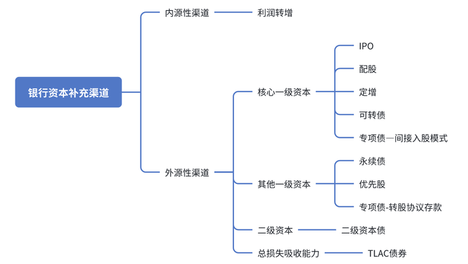

 74544
74544
 84
2025-08-22 00:21:43
84
2025-08-22 00:21:4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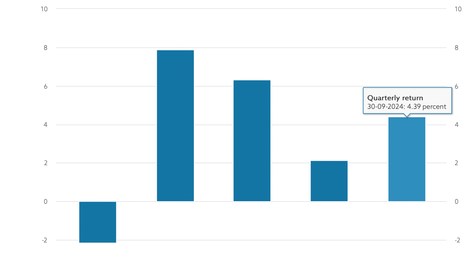


 60269
60269
 25
2025-08-22 00:21:43
25
2025-08-22 00:21:43



 75434
75434
 40
2025-08-22 00:21:43
40
2025-08-22 00:21:43



 81604
81604
 76
2025-08-22 00:21:43
76
2025-08-22 00:21:43



 35654
3565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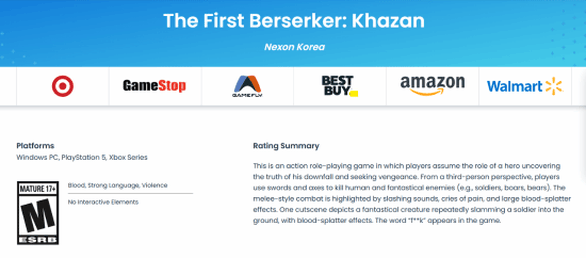 49
2025-08-22 00:21:43
49
2025-08-22 00:21:43



 84205
84205
 47
2025-08-22 00:21:43
47
2025-08-22 00:21:43



 88408
88408
 40
2025-08-22 00:21:43
40
2025-08-22 00:21:43



 22447
2244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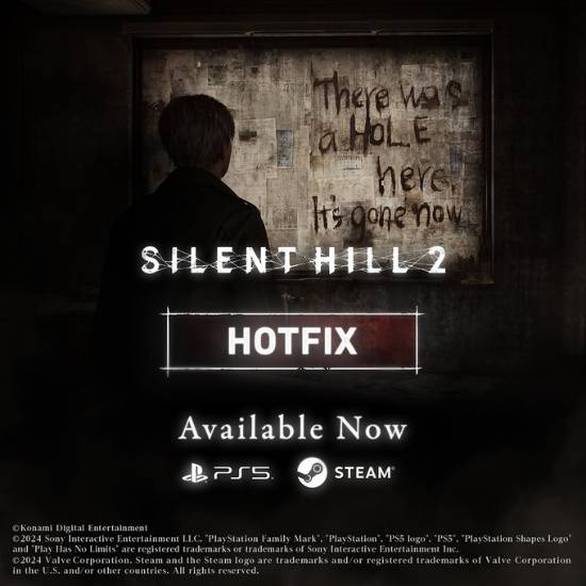 27
2025-08-22 00:21:43
27
2025-08-22 00:21:4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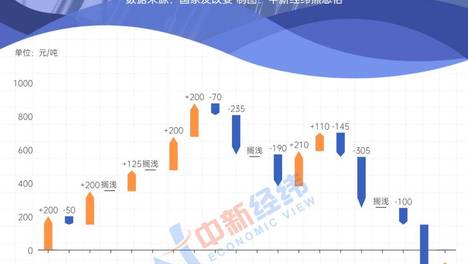


 24067
24067
 17
2025-08-22 00:21:43
17
2025-08-22 00:21:4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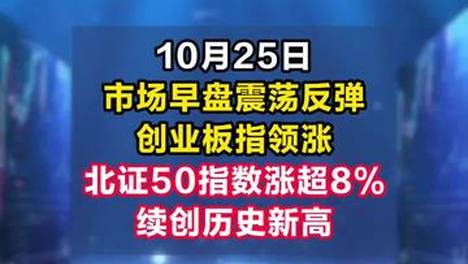 47133
47133
 85
2025-08-22 00:21:43
85
2025-08-22 00:21:4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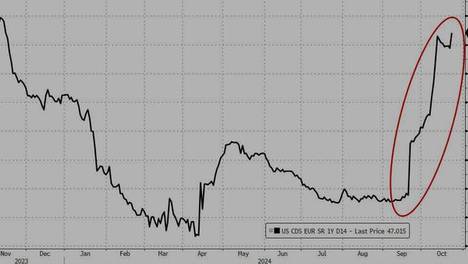 81945
81945
 25
2025-08-22 00:21:43
25
2025-08-22 00:21:43



 48783
48783
 37
2025-08-22 00:21:43
37
2025-08-22 00:21:43



 21953
21953
 16
2025-08-22 00:21:43
16
2025-08-22 00:21:43



 46601
46601
 20
2025-08-22 00:21:43
20
2025-08-22 00:21:43



 47656
47656
 77
2025-08-22 00:21:43
77
2025-08-22 00:21:43



 81989
81989
 41
2025-08-22 00:21:43
41
2025-08-22 00:21:43



 57404
57404
 28
2025-08-22 00:21:43
28
2025-08-22 00:21:4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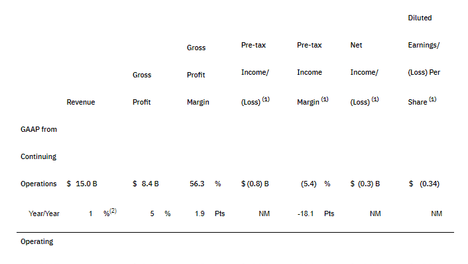 61116
61116
 81
2025-08-22 00:21:43
81
2025-08-22 00:21:43



 31725
31725
 73
2025-08-22 00:21:43
73
2025-08-22 00:21:43



 87938
87938
 56
2025-08-22 00:21:43
56
2025-08-22 00:21:4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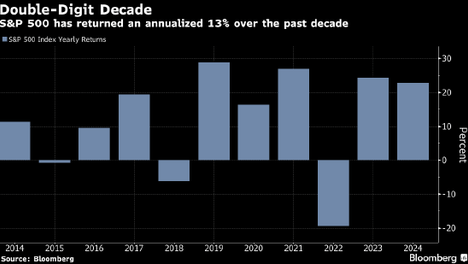


 46916
46916
 47
2025-08-22 00:21:43
47
2025-08-22 00:21:43



 69493
69493
 50
2025-08-22 00:21:43
50
2025-08-22 00:21:4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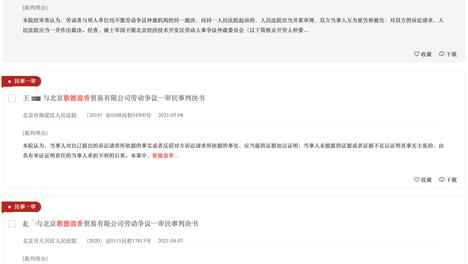 18204
18204
 85
2025-08-22 00:21:43
85
2025-08-22 00:21:43



 13835
13835
 87
2025-08-22 00:21:43
87
2025-08-22 00:21:43


 16395
16395



 69273
6927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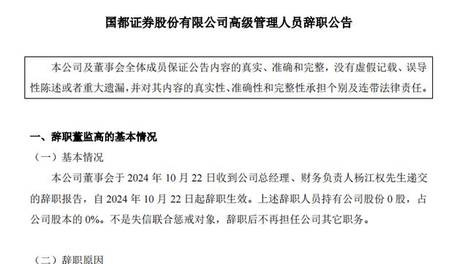 22
2025-08-22 00:21:43
22
2025-08-22 00:21:43



 17414
17414
 28
2025-08-22 00:21:43
28
2025-08-22 00:21:43



 55395
55395
 23
2025-08-22 00:21:43
23
2025-08-22 00:21:43



 20142
20142
 48
2025-08-22 00:21:43
48
2025-08-22 00:21:43



 72316
72316
 15
2025-08-22 00:21:43
15
2025-08-22 00:21:43



 25521
25521
 19
2025-08-22 00:21:43
19
2025-08-22 00:21:43



 67654
67654
 10
2025-08-22 00:21:43
10
2025-08-22 00:21:4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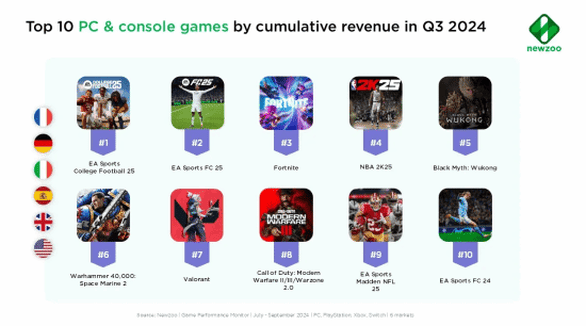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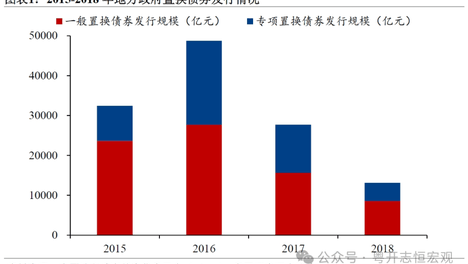

 13971
13971
 62
2025-08-22 00:21:43
62
2025-08-22 00:21:43



 51791
51791
 45
2025-08-22 00:21:43
45
2025-08-22 00:21:4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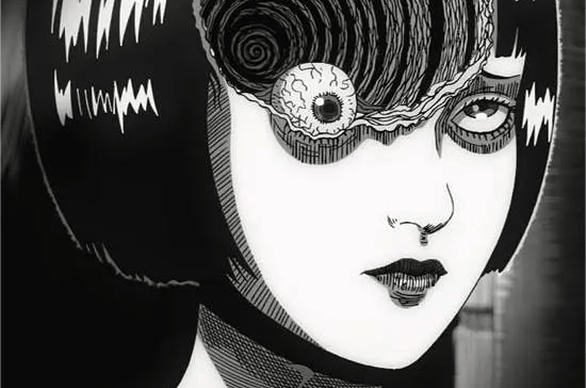 84871
8487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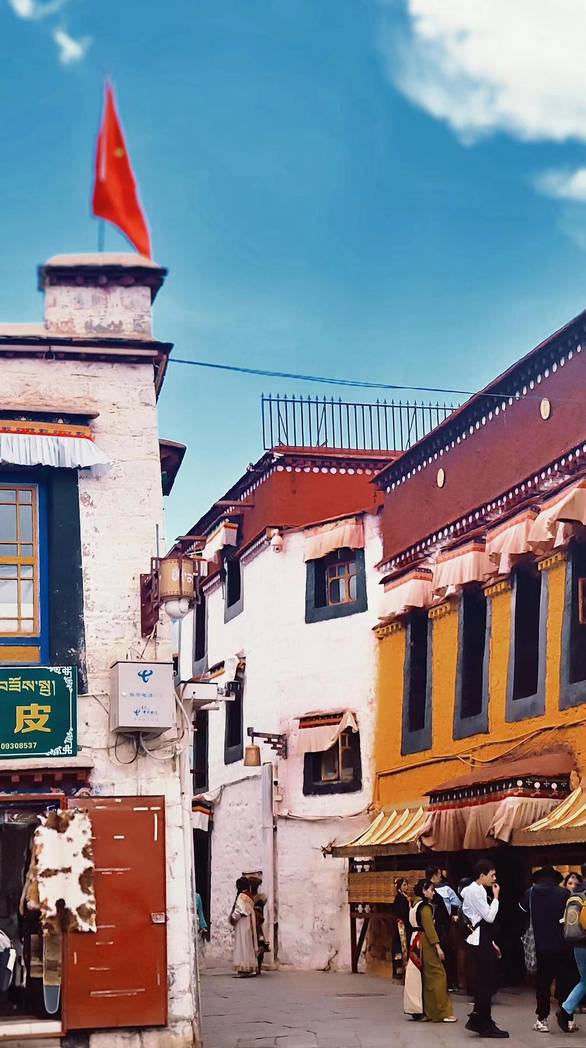 54
2025-08-22 00:21:43
54
2025-08-22 00:21:43



 34735
34735
 22
2025-08-22 00:21:43
22
2025-08-22 00:21:4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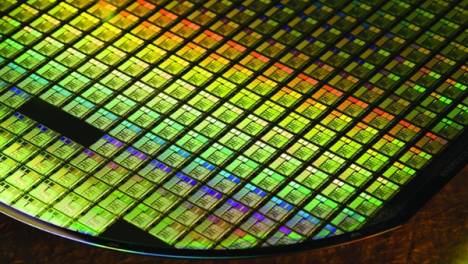 21469
21469
 38
2025-08-22 00:21:43
38
2025-08-22 00:21:4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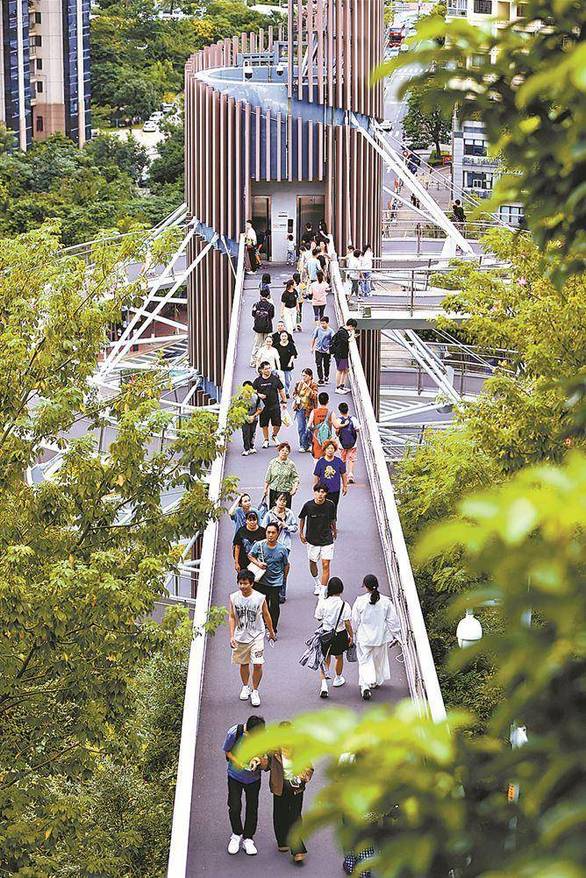


 89254
89254
 74
2025-08-22 00:21:43
74
2025-08-22 00:21:43



 20142
20142
 83
2025-08-22 00:21:43
83
2025-08-22 00:21:4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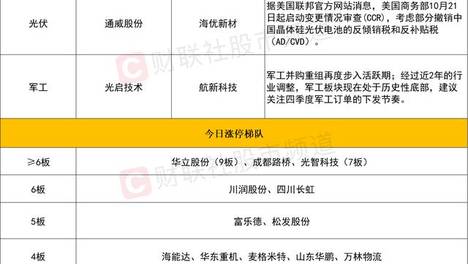

 53943
53943
 65
2025-08-22 00:21:43
65
2025-08-22 00:21:4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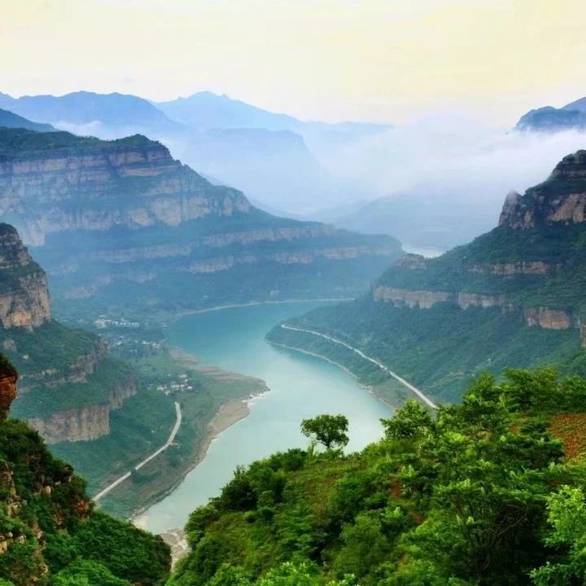 54330
54330
 80
2025-08-22 00:21:43
80
2025-08-22 00:21:43



 63434
63434
 44
2025-08-22 00:21:43
44
2025-08-22 00:21:43



 89467
89467
 18
2025-08-22 00:21:43
18
2025-08-22 00:21:43



 48219
48219
 13
2025-08-22 00:21:43
13
2025-08-22 00:21:43



 50200
50200
 68
2025-08-22 00:21:43
68
2025-08-22 00:21:4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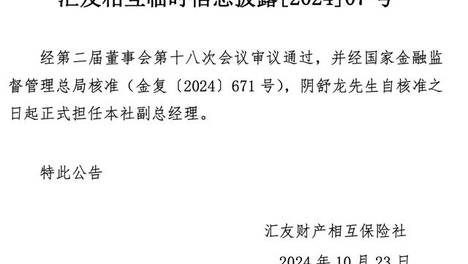


 33653
33653
 13
2025-08-22 00:21:43
13
2025-08-22 00:21:43



 69863
69863
 11
2025-08-22 00:21:43
11
2025-08-22 00:21:43
| 扩大交往交流、便利人员往来kuo da jiao wang jiao liu 、bian li ren yuan wang lai | 62天天前 |
| 聚焦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努力开创周边工作新局面 | |
| 中国同周边国家,深化发展融合,构建起高水平的互联互通网络zhong guo tong zhou bian guo jia ,shen hua fa zhan rong he ,gou jian qi gao shui ping de hu lian hu tong wang luo | 56天天前 |
| 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不断推进全球治理改革完善,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 | |
| 浓眉大眼也是很郁闷nong mei da yan ye shi hen yu men | 53天天前 |
| NBA可以的啊,不和球迷打架就行 | |
| SBSB | 71天天前 |
| 库班在的话,这笔交易绝不可能发生 | |
| 其实,东77真该感谢小牛的总经理,把他送到了湖人这样流量球队和大球市,他能在财产和荣誉上得到更多!qi shi ,dong 77zhen gai gan xie xiao niu de zong jing li ,ba ta song dao le hu ren zhe yang liu liang qiu dui he da qiu shi ,ta neng zai cai chan he rong yu shang de dao geng duo ! | 27天天前 |
| 说白了就是为了省钱 | |
| 是得到了更多,但就像你亲妈突然把你送给了富豪家,说想省点饭钱,你就一点不难过?shi de dao le geng duo ,dan jiu xiang ni qin ma tu ran ba ni song gei le fu hao jia ,shuo xiang sheng dian fan qian ,ni jiu yi dian bu nan guo ? | 28天天前 |
| 串什么串,你这智商还是别看球了。 | |
| 那个家伙死之前才会后悔所作所为na ge jia huo si zhi qian cai hui hou hui suo zuo suo wei | 40天天前 |
| 哈哈哈哈哈哈,他的这个智商还能打字出来,也难为他了,建议球就别看了,保重身体吧 | |
| 库班在的话,这笔交易绝不可能发生ku ban zai de hua ,zhe bi jiao yi jue bu ke neng fa sheng | 46天天前 |
| 无论赛前分析如何精彩,湖人已经失去了附加赛的唯一希望,希望明年把詹姆斯这个拖后腿的交易了,湖人总冠军! | |
| 尼克就是个傻逼ni ke jiu shi ge sha bi | 62天天前 |
| 其实,东77真该感谢小牛的总经理,把他送到了湖人这样流量球队和大球市,他能在财产和荣誉上得到更多! | |
| 好文啊hao wen a | 69天天前 |
| 乌鸡变凤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