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您访问的链接即将离开“江门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 是否继续?
继续访问放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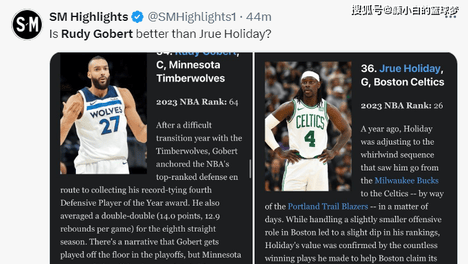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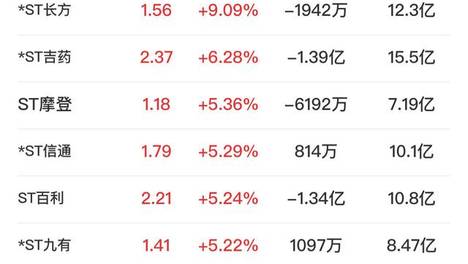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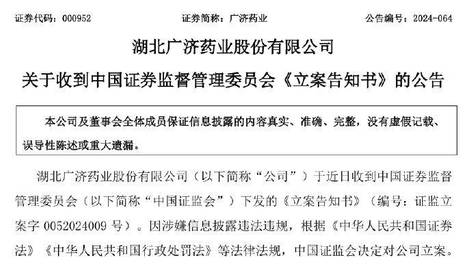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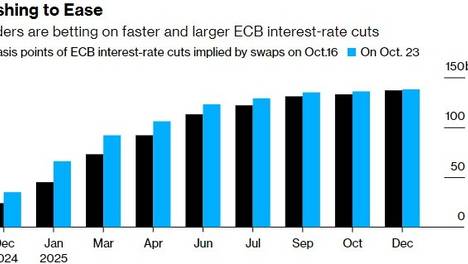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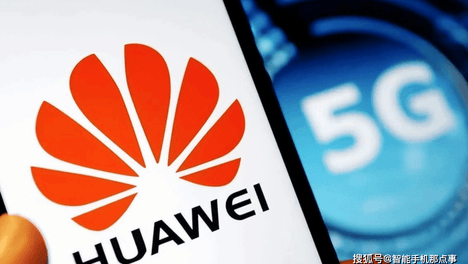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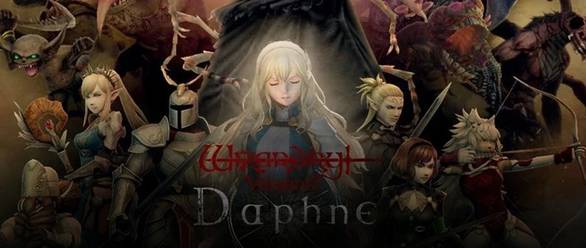


 72890
728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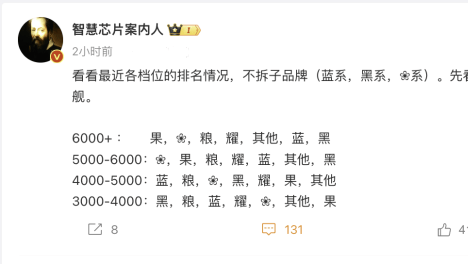 77
2025-07-20 01:24:48
77
2025-07-20 01:24:48



 73205
73205
 51
2025-07-20 01:24:48
51
2025-07-20 01:24:48



 74642
74642
 56
2025-07-20 01:24:48
56
2025-07-20 01:24: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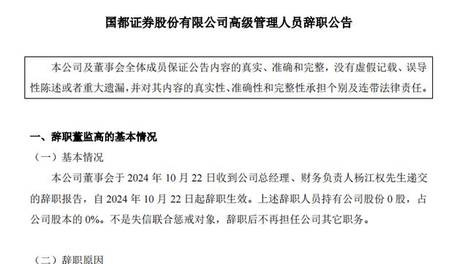

 78994
78994
 79
2025-07-20 01:24:48
79
2025-07-20 01:24: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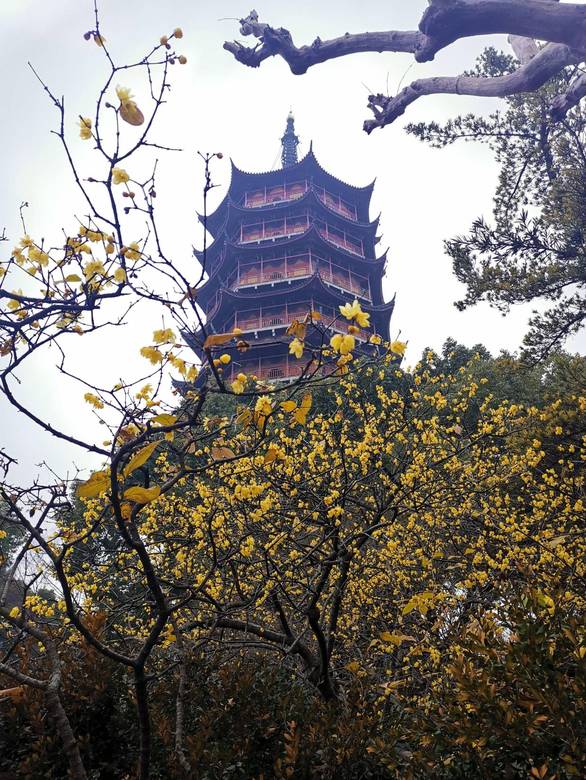

 83347
83347
 33
2025-07-20 01:24:48
33
2025-07-20 01:24: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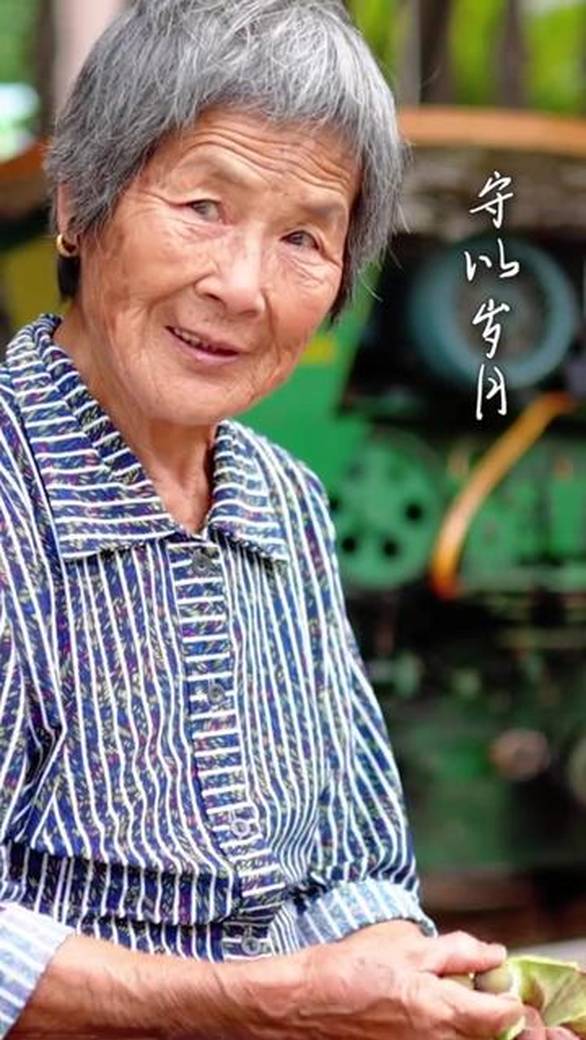


 12758
12758
 56
2025-07-20 01:24:48
56
2025-07-20 01:24: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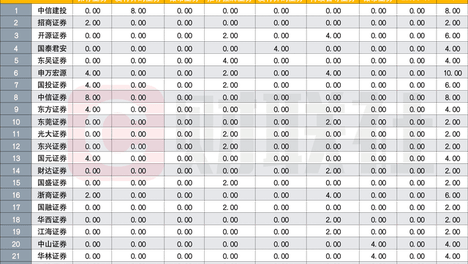

 76732
76732
 23
2025-07-20 01:24:48
23
2025-07-20 01:24: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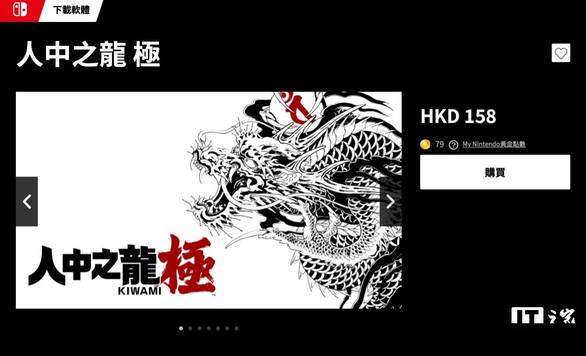

 61024
61024
 80
2025-07-20 01:24:48
80
2025-07-20 01:24:48



 18829
18829
 61
2025-07-20 01:24:48
61
2025-07-20 01:24: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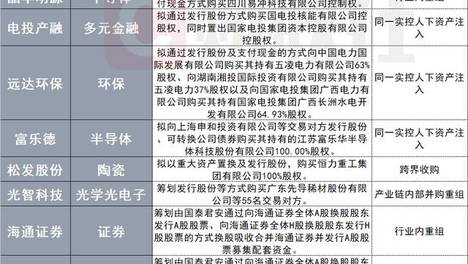 18379
18379
 13
2025-07-20 01:24:48
13
2025-07-20 01:24:48



 27307
27307
 30
2025-07-20 01:24:48
30
2025-07-20 01:24:48



 50002
50002
 86
2025-07-20 01:24:48
86
2025-07-20 01:24: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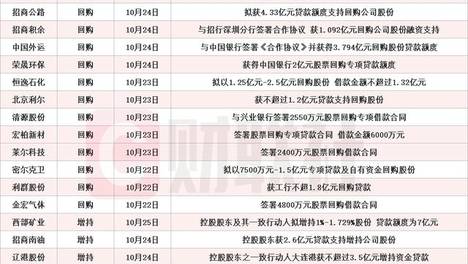


 37030
37030
 37
2025-07-20 01:24:48
37
2025-07-20 01:24: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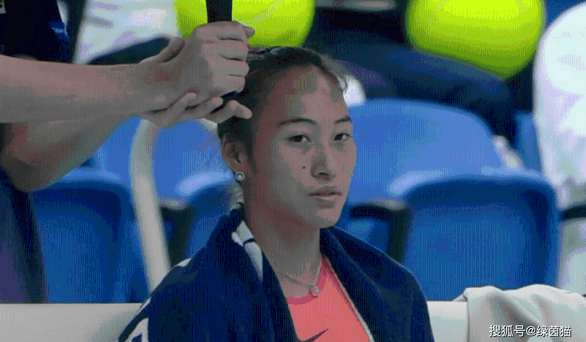 54029
54029
 76
2025-07-20 01:24:48
76
2025-07-20 01:24: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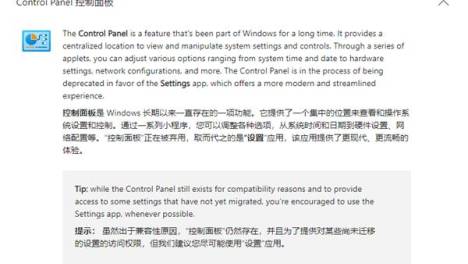 50230
50230
 44
2025-07-20 01:24:48
44
2025-07-20 01:24:48



 55107
55107
 70
2025-07-20 01:24:48
70
2025-07-20 01:24:48



 30396
30396
 75
2025-07-20 01:24:48
75
2025-07-20 01:24:48



 34259
34259
 26
2025-07-20 01:24:48
26
2025-07-20 01:24:48



 55309
5530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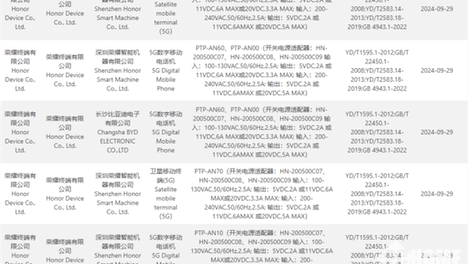 49
2025-07-20 01:24:48
49
2025-07-20 01:24:48



 83082
83082
 85
2025-07-20 01:24:48
85
2025-07-20 01:24: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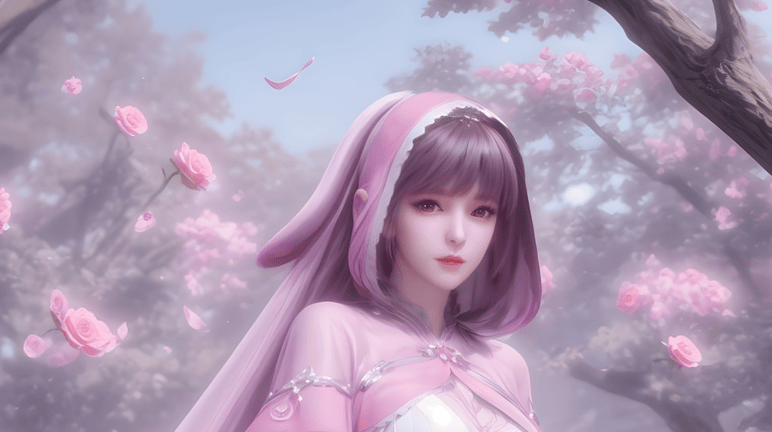 13214
132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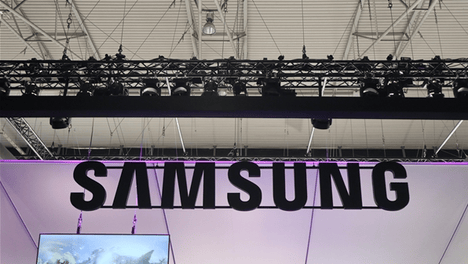 86
2025-07-20 01:24:48
86
2025-07-20 01:24: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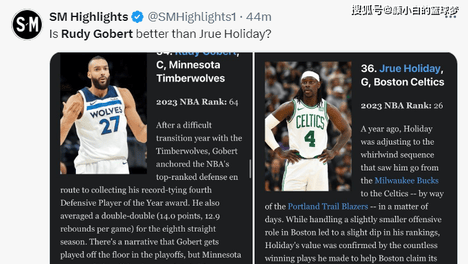

 71793
71793
 55
2025-07-20 01:24:48
55
2025-07-20 01:24:48



 13976
13976
 76
2025-07-20 01:24:48
76
2025-07-20 01:24: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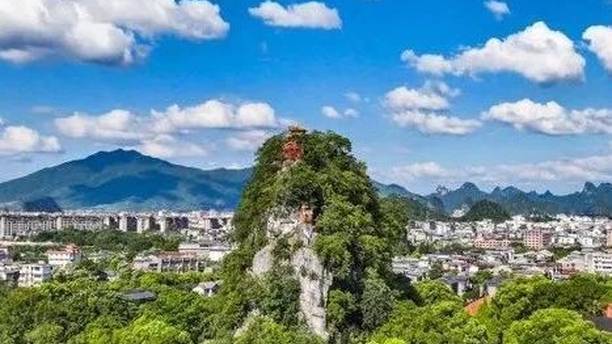 72935
7293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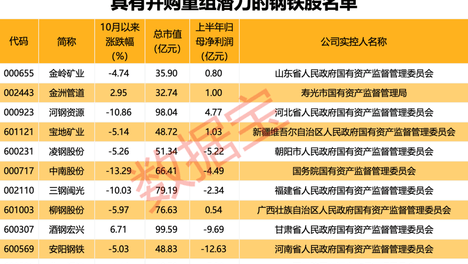 72
2025-07-20 01:24:48
72
2025-07-20 01:24:48



 42496
42496
 62
2025-07-20 01:24:48
62
2025-07-20 01:24:48



 57098
5709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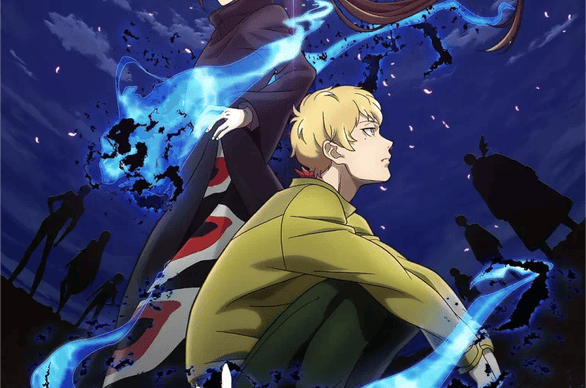 63
2025-07-20 01:24:48
63
2025-07-20 01:24:48



 49642
4964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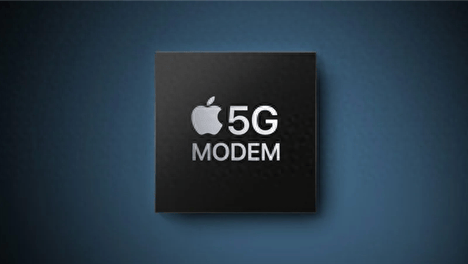 73
2025-07-20 01:24:48
73
2025-07-20 01:24: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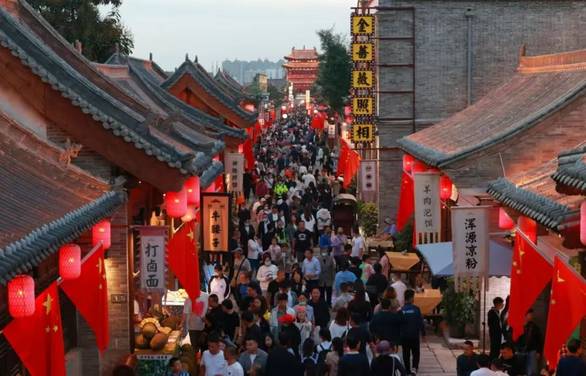

 79899
79899
 60
2025-07-20 01:24:48
60
2025-07-20 01:24:48



 16623
16623
 77
2025-07-20 01:24:48
77
2025-07-20 01:24:48



 53769
53769
 34
2025-07-20 01:24:48
34
2025-07-20 01:24: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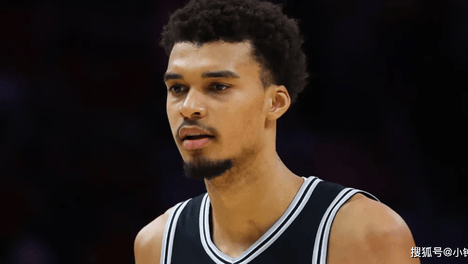

 73471
73471
 20
2025-07-20 01:24:48
20
2025-07-20 01:24: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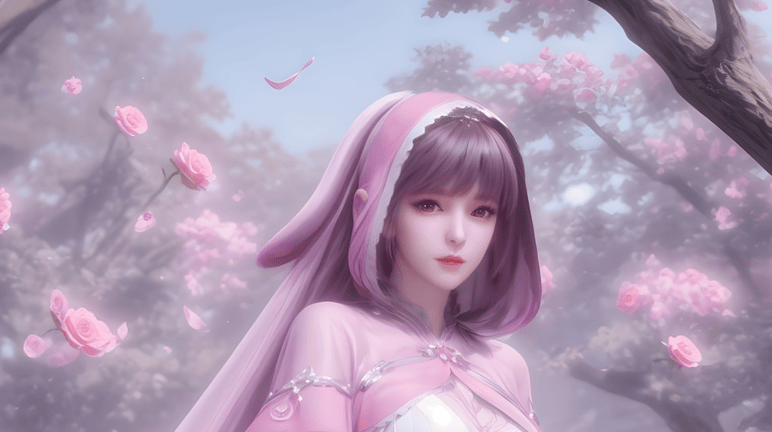

 24096
24096
 16
2025-07-20 01:24:48
16
2025-07-20 01:24:48



 80139
80139



 30994
3099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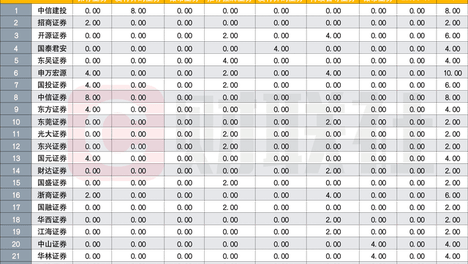 83
2025-07-20 01:24:48
83
2025-07-20 01:24:48



 62121
62121
 44
2025-07-20 01:24:48
44
2025-07-20 01:24:48



 32488
32488
 36
2025-07-20 01:24:48
36
2025-07-20 01:24: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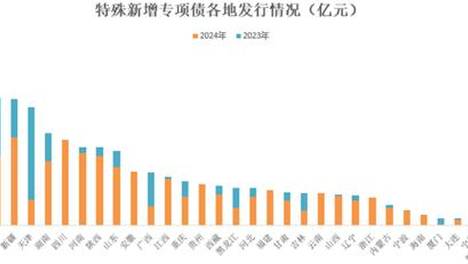

 61536
61536
 58
2025-07-20 01:24:48
58
2025-07-20 01:24: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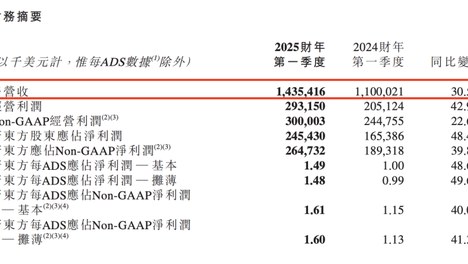


 78980
78980
 23
2025-07-20 01:24:48
23
2025-07-20 01:24: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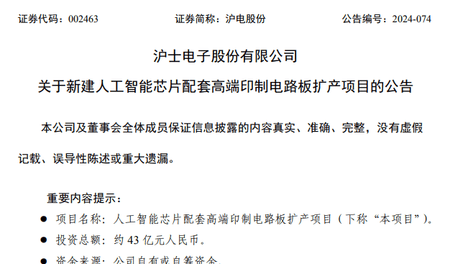


 24170
24170
 17
2025-07-20 01:24:48
17
2025-07-20 01:24: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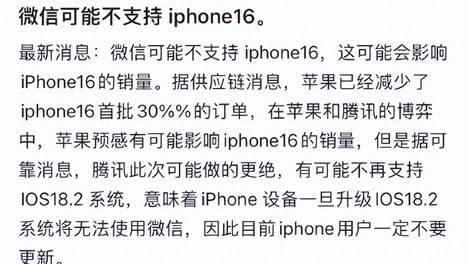 29194
29194
 74
2025-07-20 01:24:48
74
2025-07-20 01:24:48



 22852
22852
 70
2025-07-20 01:24:48
70
2025-07-20 01:24:48



 27575
27575
 68
2025-07-20 01:24:48
68
2025-07-20 01:24:48



 34156
34156
 83
2025-07-20 01:24:48
83
2025-07-20 01:24:48


 57463
57463
 51
2025-07-20 01:24:48
51
2025-07-20 01:24:48



 22076
2207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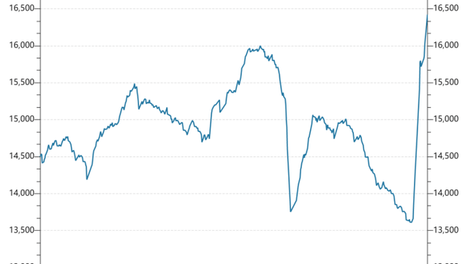 83
2025-07-20 01:24:48
83
2025-07-20 01:24: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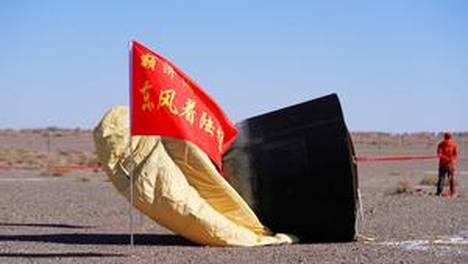

 14727
14727
 21
2025-07-20 01:24:48
21
2025-07-20 01:24: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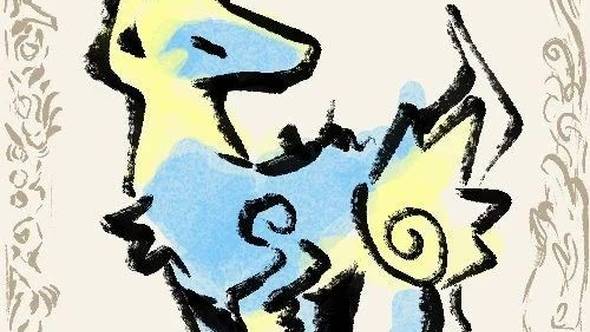


 65753
65753
 23
2025-07-20 01:24:48
23
2025-07-20 01:24:48



 70163
70163
 20
2025-07-20 01:24:48
20
2025-07-20 01:24:48



 41724
41724
 40
2025-07-20 01:24:48
40
2025-07-20 01:24:48



 71922
71922
 56
2025-07-20 01:24:48
56
2025-07-20 01:24:48



 46279
4627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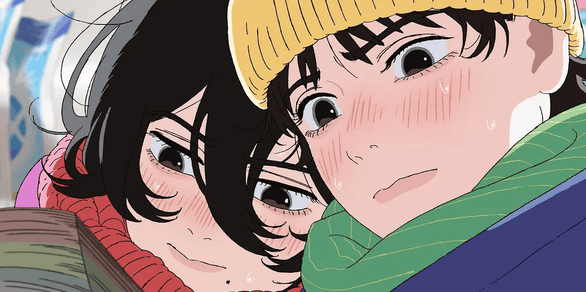 25
2025-07-20 01:24:48
25
2025-07-20 01:24:48



 39047
39047
 72
2025-07-20 01:24:48
72
2025-07-20 01:24:48



 39857
39857
 17
2025-07-20 01:24:48
17
2025-07-20 01:24: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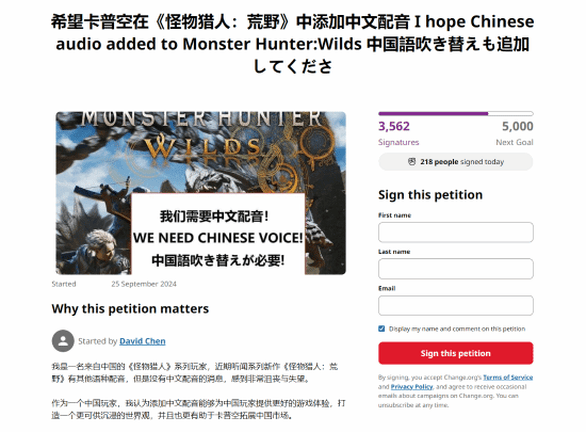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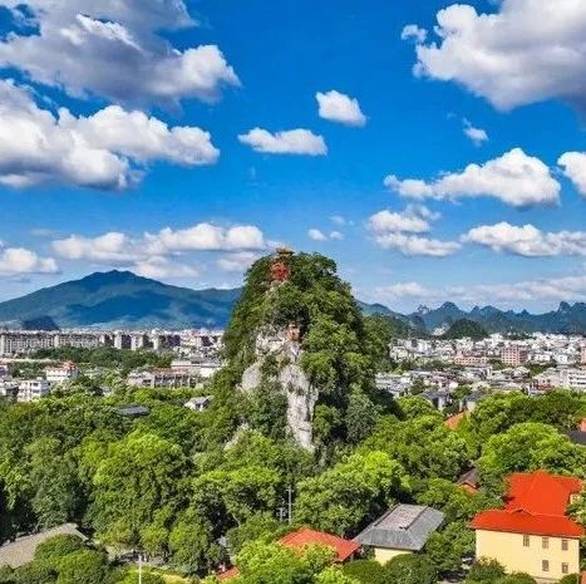 86156
86156
 26
2025-07-20 01:24:48
26
2025-07-20 01:24:48
| 胡说八道!hu shuo ba dao ! | 66天天前 |
| 人家既要当XX,又要立牌坊 | |
| 嫖娼合法了还怎么收罚款呢piao chang he fa le hai zen me shou fa kuan ne | 33天天前 |
| 穷人叫嫖娼,,,富人叫风流潇洒,,,,都是嫖,,,,只能压迫穷人 | |
| 严重怀疑这场比赛前双方是打了电话的,友谊赛?默契球?yan zhong huai yi zhe chang bi sai qian shuang fang shi da le dian hua de ,you yi sai ?mo qi qiu ? | 24天天前 |
| 为何每次受伤的总是三镇,打山东也是这样。裁判能不能好好吹个公平的比赛! | |
| 就是默契球,那种情况下三镇队禁区内手球真找不到合理的理由,大概率就是故意送一个点球,大家各拿一分jiu shi mo qi qiu ,na zhong qing kuang xia san zhen dui jin qu nei shou qiu zhen zhao bu dao he li de li you ,da gai lv jiu shi gu yi song yi ge dian qiu ,da jia ge na yi fen | 60天天前 |
| 这场球,武汉打的太好了。成都两个球都不算自己打进的 | |
| 把李铁再提审一次,问一下今天的裁判有没有分钱ba li tie zai ti shen yi ci ,wen yi xia jin tian de cai pan you mei you fen qian | 29天天前 |
| 看看三镇这草地,把自己家球员都伤了 | |
| 武汉这烂草地,什么球员能发挥好了wu han zhe lan cao di ,shen me qiu yuan neng fa hui hao le | 72天天前 |
| 1 | |
| 成都蓉城中后卫如同虚设,盯人不紧是最大的问题。cheng dou rong cheng zhong hou wei ru tong xu she ,ding ren bu jin shi zui da de wen ti 。 | 61天天前 |
| 你知道个屁?球场本身好得很,连日暴雨,晚上没下正常比赛老天爷给面子了!啥都不知道,只知道驴叫 | |
| 徐正源本场比赛换下罗慕洛就是一个错误,上一场比赛打进五个球不换下罗慕洛休息,本场比赛在1:1的微妙情况下却换下了中场核心罗慕洛,结果罗慕洛刚换下对方就进球了。xu zheng yuan ben chang bi sai huan xia luo mu luo jiu shi yi ge cuo wu ,shang yi chang bi sai da jin wu ge qiu bu huan xia luo mu luo xiu xi ,ben chang bi sai zai 1:1de wei miao qing kuang xia que huan xia le zhong chang he xin luo mu luo ,jie guo luo mu luo gang huan xia dui fang jiu jin qiu le 。 | 28天天前 |
| 就是默契球,那种情况下三镇队禁区内手球真找不到合理的理由,大概率就是故意送一个点球,大家各拿一分 | |
| 把李铁再提审一次,问一下今天的裁判有没有分钱ba li tie zai ti shen yi ci ,wen yi xia jin tian de cai pan you mei you fen qian | 88天天前 |
| 为何每次受伤的总是三镇,打山东也是这样。裁判能不能好好吹个公平的比赛! | |
| 看下这个裁判有多黑,收了蓉城多少?太明显的照顾蓉城。kan xia zhe ge cai pan you duo hei ,shou le rong cheng duo shao ?tai ming xian de zhao gu rong cheng 。 | 42天天前 |
| 罚一万,扣十分就没错了 | |